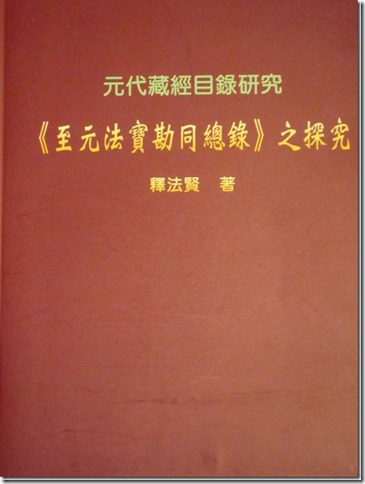本文引自《福嚴佛學研究》第八期,123-185頁,讀者請自行前往下載:
http://www.fuyan.org.tw/download/FBS_vol8-4.pdf
====================
初期漢譯佛典疑難詞釋義
Some Notes Regarding the So-called ‘Difficult Phrases’ in Those Earlier Sūtras Translated during Han and Jin Dynasty
佛教論文翻譯作家
蘇錦坤
摘要
現存漢語大藏經漢晉之間的「古譯經典」,或者譯文用字生僻,或者譯文用字並非生僻,只是詞義已經變遷而容易造成讀者誤解。這些「疑難詞」可以分為兩類詞彙,一類是可以藉由近代學者對漢文典籍的訓詁研究,來追溯漢魏兩晉譯經的古義,也就是說,必須在漢語典籍中得到「確詁」,較難從梵語或巴利佛教文獻得到助益;另一類則是詞意晦澀,無法從漢語典籍得到合理的詮釋,只能藉助跨語言文本的對勘,在其他語言文本上定位此一譯詞的可能用字,進而推敲其對應意涵與翻譯用語。本文列舉一些經例來闡述這些特殊詞彙的詮釋。
In Chinese Tripitakas there are ‘difficult’ words or phrases in suttas which were translated between Han and Jin dynasty. These words or phrases are difficult to gain ‘precise’ or ‘proper’ meaning. Though some of them did not adopt rare characters at all, the meaning of them had migrated with times, and became different with conventional meaning nowadays. We may put these words or phrases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is to have them expounded in the ligh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books, the other is to find clues for explanations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ies. This article raises some examples of these two categories for detail examination.
關鍵詞:阿含、漢巴對應經典、佛典字詞釋義
一、前言
漢、晉之間的翻譯佛典常有一些字詞艱澀深奧、生僻難解。對於這些難字、難詞的解析,有一部分可以從漢語古文獻來掌握其詞義,此一時期的譯語有一些詞義已經變遷,未經適當的詮釋難以理解其原意。[1]另外,有一些譯詞用字並不生僻,字義並不難解,但是詞義似乎與整段經文齟齬不順,這類詞彙應該透過跨語言的文本對勘,從對應經典或相當的「定型句」來確認此漢譯字詞的對應梵、巴字彙,進而解讀此一漢譯字詞的詞意。
繼〈《雜阿含經》字句斠勘〉和〈漢譯佛典校勘舉例---兼論印順導師與佛典校勘〉(與溫宗堃合著)兩篇論文之後,[2]筆者在本文舉例探討:「在佛典校勘學訂正訛誤或並存異說的基礎上,如何正確地掌握漢譯詞彙的意涵,進而探索經義」。
在佛經音義研究上,從唐朝玄應法師的《眾經音義》、慧琳法師的《一切經音義》、宋朝希麟法師《續一切經音義》以下,當代中國學者在佛典語言學上已有相當的成就,如李維琦的《佛經釋詞》、《佛經續釋詞》、《佛經詞語彙釋》,[3]以及方一新、顧滿林、徐時儀、朱慶之、董志翹、胡敕瑞、梁曉虹等人的佛典漢語研究。筆者在閱讀經典時陸續登錄一些字詞釋例,這些釋例或者是受到上述書籍論文所啟發,或者是上述文獻、論文所未收的詞義,或者是藉助巴利文獻補充前人的此類著述,在此以「野人獻曝」的心情來與讀者分享這些零散的札記。
為了行文簡潔,本文將印順法師的《雜阿含經論會編》簡稱為《會編》,將赤沼智善《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簡稱為《互照錄》,Rhys Davids, T. W. and Stede, William, (1925), Pali-English Dictionary,簡稱為PED,除非特別標註,本文所引《雜阿含經》都是指求那跋陀羅譯的五十卷本《雜阿含經》(T99)。
二、藉助巴利文獻解讀詞義
初期漢譯經典有一些用詞可以明顯判斷是出自翻譯,可以從《一切經音義》、《翻梵語》、《翻譯名義集》之類的書籍查閱字義,[4]或者利用漢、巴、梵對應經文的啟示,找出字義。
但是,也有部分譯詞因為輾轉抄寫而造成訛誤,無法辨識原來的詞意;或者因為譯詞用字簡易,容易被誤認為土生土長的漢語。如果未參考跨語言文本的對應經文,這樣的字詞容易遭誤解、誤釋。
以下筆者所舉的經文例句,都不宜「望文生訓」,硬用漢語訓詁方法來詮釋,而是應該作為「翻譯詞彙」,藉助梵、巴佛教文獻來解讀詞義。
1.《雜阿含•267經》:嗟蘭那鳥
《雜阿含•267經》:
佛告比丘:「如嗟蘭那鳥種種雜色,我說彼心種種雜亦復如是。所以者何?彼嗟蘭那鳥心種種故其色種種。是故,當善觀察思惟於心長夜種種,貪欲、瞋恚、愚癡種種,心惱故眾生惱,心淨故眾生淨。譬如畫師、畫師弟子,善治素地,具眾彩色,隨意圖畫種種像類。」[5]
在上引經文中,似乎是舉例解說「如『嗟蘭那鳥』種種雜色,心亦有種種雜(染)」之後,又舉「畫師、弟子」繪畫為例,他們先在牆壁、木板、畫布塗上素色背景,再畫上各種形象、各種色彩。如此理解的話,「嗟蘭那鳥」是一事,「畫師、弟子繪畫」又是另一事,經文舉兩件事作說明。
上述引文中「是故,當善觀察思惟於心,長夜種種貪欲、瞋恚、愚癡種種」,文句怪異,不像漢語句型。《會編》主張應作:「是故,當善觀察思惟於心,長夜種種貪欲、瞋恚、愚癡所染。」[6]
《會編》經常依據同一經中的其他文句結構來進行校勘。例如,引文之前有兩段如此的經文:「長夜心為貪欲所染,瞋恚、愚癡所染故。」與「當善思惟觀察於心。諸比丘!長夜心貪欲所染,瞋恚、愚癡所染。」[7]
由此可知,應如《會編》的主張,引文的第二個「種種」應作「所染」。本文遵從此說。
經文「如嗟蘭那鳥種種雜色,我說彼心種種雜亦復如是。所以者何?彼嗟蘭那鳥心種種故其色種種。」,巴利對應經文為:
‘Diṭṭhaṃ vo, bhikkhave, “caraṇaṃ nāma cittaṃ”ti?’ ‘Evaṃ, bhante’. ‘Tampi kho, bhikkhave, caraṇaṃ nāma cittaṃ citteneva cittitaṃ. Tenapi kho, bhikkhave, caraṇena cittena cittaññeva cittataraṃ.’ [8]
(「諸比丘!你們見過稱為『嗟蘭那』的圖畫嗎?」「見過。世尊!」「諸比丘!即使稱為『嗟蘭那』的圖畫有種種顏色,諸比丘!心的思維比『嗟蘭那』圖畫的顏色更多樣。」)[9]
菩提比丘指出,上述經文含有數個雙關語,citta具有「心」與「圖畫」兩種意涵;caraṇaṃ citta具有「帶著去旅行的圖畫」與「思考的心」的雙重意思。cittita對於「心」而言意指「思想、思維」,對於「圖畫」而言意指「種種的」。
陳明指出Citrasena一詞,義淨譯為「彩軍」,從梵、漢本《孔雀王咒經》的對照,可以發現僧伽婆羅將Citrasena一詞譯為:「質多羅仙那夜叉(梁言種種軍)」。[10]也就是說,漢譯者會把相當於「citta, citra」的字,理解為「色彩」或「種種的」兩種字義。
Citta解釋為「種種的」的字義可以從《法句經》的相關譯文得到佐證。巴利《法句經》171頌:
Etha passathimaṃ lokaṃ, cittaṃ rājarathūpamaṃ;
Yattha bālā visīdanti, natthi saṅgo vijānataṃ.
在古譯,“cittaṃ rājarathūpamaṃ”是譯作「如王雜色車」,所以,相當於citta的字有可能被翻譯作「種種色」。[11]
筆者認為《雜阿含•267經》「嗟蘭那鳥」可能是「嗟蘭那圖」的訛寫,只是這僅僅為個人的一項猜想而已,尚無足夠的文證可以確認此一假說。依此解釋,則經文前面說「心如『嗟蘭那鳥(圖)』種種雜色」之後,又舉「畫師、弟子」繪畫為例,只是同一件事。
以「雙關語」來講說教導的經文並不少見,《雜阿含•235經》也是類似的狀況:「有師、有近住弟子,則苦獨住,無師、無近住弟子,則樂獨住。」[12]
又如《法句經》卷2〈28 道行品〉:「斷樹無伐本,根在猶復生,除根乃無樹,比丘得泥洹。」[13]
參考巴利《法句經》283頌,也是在語音上,以「斷除林木(vana)而無森林(ni-vana)」近似「斷除貪欲(vana)則涅槃(nibbāna)」來加深聽法的印象。
這一類的經例顯示,有些經文如不藉助跨文本對照閱讀去理解其隱含的雙關語,僅僅演繹漢語詞句無法得到令人滿意的詮釋。
2.《雜阿含•471經》:食與不食
《雜阿含•715經》:
譬如身依食而立,非不食。如是五蓋依於食而立,非不食。[14]
《雜阿含•471經》:
樂食受、苦食受、不苦不樂食受,樂無食、苦無食、不苦不樂無食受。[15]
《雜阿含•472經》:
樂食受、苦食受、不苦不樂食受;樂無食受、苦無食受、不苦不樂無食受;樂貪著受、苦貪著受、不苦不樂貪著受;樂出要受、苦出要受、不苦不樂出要受。[16]
在漢譯佛教經典中,「食」有時意指「四食」,[17]此處《雜阿含•715經》「食」字,相當於巴利「āhāra」僅是指「藉以產生、增長的事物」,「不食」意指「不依食」。而《雜阿含•471經》、《雜阿含•472經》的「食」字則相當於巴利「sāmisa」,意為「世俗的(肉體的)」,而「無食」則是指「非世俗的」;上述《雜阿含•472經》經文列舉了「世俗的、非世俗的、出離的」三種「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18]
3.《雜阿含•506經》:騣色虛軟石
《雜阿含•506經》:
佛住三十三天驄色虛軟石上,去波梨耶多羅、拘毘陀羅香樹不遠夏安居,為母及三十三天說法。[19]
「驄色虛軟石」的確切意義頗難了解。支謙翻譯的《佛說義足經》也有類似的敘述。
《佛說義足經》:
佛在忉利天上,當竟夏月,波利質多樹花適好盛,坐濡軟石上,欲為母說經,及忉利天上諸天。[20]
《雜阿含•506經》所譯的「驄色虛軟石」很可能就是《佛說義足經》的「濡軟」或「柔軟」石。
在《佛本行集經》與《起世經》也提到三十三天波利質多羅樹下的一塊大石。
《佛本行集經》〈57 難陀出家因緣品〉:
從香醉山沒身往至三十三天,現於波利質多羅樹。時,彼樹下有一大石,名曰婆奴唫(逆林反)摩羅(隋言黃褐),住於彼處。[21]
《起世經》〈8 三十三天品〉:
彼波利夜怛邏拘毘陀羅樹下,有天子住,名曰末多,日夜常以彼天種種五欲功德,具足和合遊戱受樂。是故諸天,遂稱彼樹,以為波利夜怛邏拘毘陀羅。復次,諸比丘!三十三天,縱有急疾,未曾肯捨般荼甘婆石,必設供養尊重恭敬,然後乃復隨意而去。[22]
《佛說立世阿毘曇論》與《大智度論》也提到波利質多樹附近的一塊大石,可是並不確定是在三十三天。
《佛說立世阿毘曇論》〈25 大三災品〉:
波利質多樹及俱毘羅羅園,由乾陀海、由乾陀山,伊沙陀海、山,佉羅胝海、山,善見海、山,馬耳海、山,毘那多海、山,尼民陀海、山,及四天下中間洲地掘成州海,起鐵圍山。如是樹及拘毘羅羅園,此中昔是「般住劍婆羅寶石」。[23]
《大智度論》:
又在天上歡喜園中,夏安居時,坐「劍婆石」,柔軟清潔,如天綩綖,亦不以為樂。[24]
關於「劍婆石」,《翻梵語》註解為「毺燈」:「劍婆石(應云劍婆羅,譯曰毺燈)。」[25]「毺燈」應寫作「毺(毛*登)」,意為「細緻的毛織品為」。
《一切經音義•四分律音義》:「《通俗文》:『織毛褥曰[(〦/(目*目)/大)*毛]毺,細者謂之毾[登*毛]也。』」[26]
依照以上所引,如果「劍婆石」是「劍婆羅」的類似譯名,而且是一種毛織品,就和巴利「kambala」相當。[27]巴利「paṇḍukambala」相當於上引《佛說立世阿毘曇論》的「般住劍婆羅」與《起世經》的「般荼甘婆石」,意為橘色或淺紅色的毛織品。[28]而《佛本行集經》的「婆奴唫摩羅」很可能是相當於巴利「vālakambala」,意為「馬尾或馬騣編成的毛織品」,[29]這可能是《雜阿含•506經》「驄色虛軟石」的「驄」字的來源,筆者推測「驄色虛軟」或「驄色柔軟」可能是相當於的「vālakambala」的對譯。
《雜阿含•264經》:「八萬四千寶馬,唯乘一馬,名婆羅訶,毛尾紺色。」[30]
《增壹阿含•50.4經》:「見有紺馬王,名婆羅含(秦言『髮烏朱毛尾』),乘空而來,行不動身。」[31]
《雜阿含•264經》馬名「婆羅訶」應為「婆羅含」,全名應為「婆羅含婆羅vālakambala」,此馬的馬尾毛是暗紅色(紺),也就是《增壹阿含•50.4經》「秦言『髮烏朱毛尾』」的本意。
邱大剛先生提醒筆者,Malalasekara的《巴利專有名詞詞典》在Sakka處提到「the Paṇḍukambalasilāsana, composed of yellow stone. (Paṇḍukambalasilāsana為黃色石頭所作)」。Paṇḍukambala-silāsana,silā是石頭,sana是布,雖然不能確定是「像布的石頭」或「像石頭的布」,「石」字是本來的字義,不是漢譯所添加。[32]
4.《雜阿含•612經》:補寫
《雜阿含•612經》:
如是如來四種聲聞,增上方便,利根智慧,盡百年壽,於如來所百年說法教授,唯除食息、補寫、睡眠,中間常說、常聽;智慧明利,於如來所說,盡底受持,無諸障閡,於如來所不加再問。[33]
「補寫」的「寫」字,《元普寧藏》與《明徑山藏》作「瀉」字,即使如此,似乎並未對解釋經義提供有效的線索。
檢閱經文,在《中阿含•163經》與《佛說身毛喜豎經》各有一段提到善射之人的經文:
《中阿含•163經》:
猶如四種善射之人,挽彊俱發,善學善知,而有方便,速徹過去。如是,世尊有四弟子,有增上行、有增上意、有增上念、有增上慧,有辯才成就第一辯才,壽活百歲,如來為彼說法滿百年,除飲食時、大小便時、睡眠息時及聚會時。[34]
《佛說身毛喜豎經》:
譬如力士持挽硬弓端直而射,悉獲中的。……舍利子,今我法中聲聞弟子,一能請問而無有載。又復一聞我說,不能於中審解所說文句義理,況復末世餘諸弟子,若時飲食、嗜著其味、睡眠疲倦、運動憩止、大小便事,諸所施作?[35]
此段《中阿含•163經》引文與《雜阿含•612經》經文結構近似,前者是說如來說法無窮無盡,後者則是說如來演說四念處無窮無盡,兩者可以說是同一樣式的「定型句pericope」。《中阿含•163經》經文「除飲食時、大小便時、睡眠息時及聚會時」,雖然多了「聚會時」,兩相對照,仍然可以辨識出《雜阿含•612經》位於「補寫」的位置是「大小便」,因此《元普寧藏》與《明徑山藏》的「瀉」字,應有所本。[36]
5.《雜阿含•627經》:住於學地
《雜阿含•627經》:
佛告阿那律:「若聖弟子住於學地,未得上進安隱涅槃,而方便求,彼於爾時,當內身身觀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37]
黃優良教授的論文〈中古阿含部佛經詞語例釋〉指出,中國出版的《漢語大詞典》詞條「學地」只解釋為「猶『學田』,辦學用的土地。」此一解釋顯然不適用於此處的文義,「黃文」指出此處「學地」乃「別為一義」,但是未加予解釋。另外,「黃文」也誤將「調伏世間貪憂」錄為「調伏世間貪愛」。[38]
《雜阿含•542經》也有「在於學地」經文:
若比丘在於學地,上求安隱涅槃住,聖弟子云何修習多修習,於此法、律得盡諸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39]
此經的巴利對應經典為《相應部•52.4經》(SN 52.4),相當的經文為:
"Sekhena, avuso Anuruddha, bhikkhunā katame dhammā upasampajja vihātabbā?" [40]
巴利經文之意為「友阿那律,處於『有學』階段的比丘,應住於與修習那一法?」佛教名相稱「阿羅漢」為「無學asekha」,稱「四雙八輩賢聖」[41]的其他七階為「有學sekha」,或者泛稱所有未達到阿羅漢果的佛弟子為「有學」。所以,經文「住於學地」或「在於學地」,是指「處於尚未證得阿羅漢的修行階段」。
6.《中阿含•66經》:闕已
《中阿含•66經》:「我憶昔貧窮,唯仰捃拾活,闕已供沙門,無患最上德。」[42]
上引經文「闕已供沙門」,《大正藏》與CBETA均作「已」字,《佛光阿含藏》卻作「己」字,三處都沒有校勘註記。此一偈頌相當於在巴利《小部尼柯耶,長老偈》910偈,阿那律自敘其前生:「Annabhāro pure asiṃ, daliddo ghāsahārako; samaṇaṃ paṭipādesiṃ, upariṭṭhaṃ yasassinaṃ.過去世我是扛食物的人,赤貧的人,送食物給具有極高名譽的修行沙門的人。」
經律之中也有類似的譯詞,例如:
《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昔我曾不食,彼世時施與,遭遇見沙門,大通和莅吒。[43]
《古來世時經》:
我時心念:「朝出城時,見此緣覺入城分衛,而空鉢還,想未獲食,吾當斷食以奉施之。」[44]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鄔波難陀亦來乞食。見青蓮花便作是念:「此苾芻尼但於僧眾而興供養,亦有普意該別人耶?我今應試即就索食。尼心慇重闕己濟人,還持己分奉施尊者,同前絕食。」[45]
所以,不管是依據《中阿含•66經》經文:「我寧可自闕己食,分與此仙人。」[46]或是依據《古來世時經》:「吾當斷食以奉施之。」與《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的「昔我曾不食」,此處《中阿含•66經》偈頌應該是:「闕己」,而作「將自己的食物提出作為供養」解釋。
雖然《佛光版》的「闕己供沙門」比「闕已」合適,但是依校勘的原則,此處應該補上一個「校勘註記」。
7.《中阿含•71經》:庶幾
漢譯經典有「庶幾」兩字,詞不生僻,卻是不易解釋。傳統漢語文獻中,「庶幾」,有「幾乎接近、近於」與「期盼、希望」的意思。如《論語》〈先進〉:「回也其庶乎!屢空。」何晏《論語集解》:「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庶,近也,言近道也。」所以「回庶幾聖道」意為「顏回接近聖人之道」。[47]
《一切經音義》卷65:「庶幾(《爾雅》:『庶,幸也。』郭璞曰:『庶幾,僥倖也。』又云:『庶幾,尚也。庶,冀也;幾,微也。』)」[48]此處「庶幾」意為「冀望、期盼」。如《中本起經》:「六者、比丘尼有庶幾於道法,得問比丘僧經律之事。」[49]此處之意不是「近於道法」,而是「期望、欣盼聽聞道法」。
但是,如下列經文:
《中阿含•71經》:「汝等是我親親,作惡行,不精進,懶惰、懈怠、嫉妬、慳貪,不舒手,不庶幾,極著財物。」[50]
《增壹阿含•46.7經》:「彼王貪著財物,不肯庶幾。」[51]
隋闍那崛多翻譯的《佛本行集經》:「菩薩在胎,其菩薩母,志習庶幾,樂喜行檀。自餘眾生,在母胎時,其母慳貪,不喜布施,悋惜財物。」[52]
從《佛本行集經》的引文,「志習庶幾,樂喜行檀」與「不喜布施,悋惜財物」對比,可以推測此處「庶幾」為「施捨、布施」之意。
《中阿含•150經》:
梵志!於意云何?若有奉事,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若有奉事,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53]
在《中部 120經》提到類似的五事為「saddhā信,sīla戒,suta聞,cāga捨,paññā慧」,「庶幾」是「cāga捨」的對應經文,意義為「施捨、布施」。
筆者不明瞭為何將相當於「cāga捨」譯作「庶幾」,雖然有時「正倉院聖語版」或「宋版(南宋思溪藏)」會寫作「謶譏」,也無法協助解答此一疑問。[54]
郭忠生已經指出此詞的意涵:「在《中含》,『庶幾』是捨的異譯。」[55]
8.《中阿含•98經》:「儀容庠序」與「視瞻審諦」
漢譯《中阿含》與《增壹阿含》有多處出現「儀容庠序」或「威儀庠序」,此一詞彙不易理解。例如:
《中阿含•80經》:「當復學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申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56]
《中阿含•98經》:「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伸低昂,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57]
《中阿含•122經》:「或有癡人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申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似如真梵行,至諸真梵行所,彼或不知。」[58]
《增壹阿含•4.2經》:「我聲聞中第一比丘,威容端正,行步庠序,所謂馬師比丘是。」[59]
約同一時期不知譯人的《分別功德論》則譯為「威儀庠序」:「遙見馬師,威儀庠序,法服整齊。」[60]
「庠序」的一般解釋為「學校」,可參考《孟子》與《續一切經音義》的解釋。
《孟子》:「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61]
《續一切經音義》:「庠序(……《禮記》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上庠太學,下庠小學。』……《玉篇》云:『東序西序之學也。』《爾雅》云:『東西牆謂之序。』《郭注》云:『所以序別內外』)。」[62]
但是,《一切經音義》的另一註釋更適合此處的經文。
《一切經音義》:「庠序(……謂儀容有法度也。……《白虎通》曰:『庠之言詳也,以詳禮儀之所也。序,序長幼也。』)」[63]
所以「儀容庠序」或「威儀庠序」都是意指「儀容有法度」,容貌、衣著、舉止都合乎規矩法度,而與「學校」、「長幼有序」或「整齊的、有條理的」無關。[64]
「儀容庠序」的意涵也可以從別處經文得到啟發。
《增壹阿含•38.9經》:「有辟支佛名善目,顏貌端政,面如桃華色,視贍審諦,口作優鉢華香,身作栴檀香。」[65]
《增壹阿含•39.8經》:「若轉輪聖王出現世時,自然有此玉女寶現,顏貌端政,面如桃華色,不長不短,不白不黑,體性柔和,不行卒暴,口氣作憂鉢華香,身作栴檀香。」[66]
《菩薩從兜術天降神母胎說廣普經》:「羅睺羅阿修羅王,生女端正,具足女法六十四能。行步進止不失儀則,面如桃花色,口出言氣如優鉢蓮花香,身作牛頭栴檀香。」[67]
《增壹阿含•38.9經》、《增壹阿含•39.8經》與《菩薩從兜術天降神母胎說廣普經》的「顏貌端政,面如桃華色……身作栴檀香」可以當作一「定型句」的不同翻譯,參考下文所引的《佛本行集經》,「視瞻審諦」相當於「舉動審諦,不急不寬,住立仰瞻,人所樂覩,形服相稱,內外嚴儀」,「儀容庠序」相當於「行步進止不失儀則」、「進止端平,足步安穩,無有差移」。
《佛本行集經》〈39 耶輸陀宿緣品〉:「是人遙見彼辟支佛,威儀庠序,進止端平,足步安穩,無有差移,左右觀看,徐行直視,舉動審諦,不急不寬,住立仰瞻,人所樂覩,形服相稱,內外嚴儀。」[68]
蔣禮鴻在《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書中也指出,「庠序」又作「祥序」、「徐詳」,為「舉動安詳肅穆的意思」。[69]
9.《中阿含•99經》:息道
在四部阿含的漢譯中,「息道」只出現於三部《中阿含經》,此一詞彙的意思不易理解。此三處經文如下:
《中阿含•81經》:「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如本見息道骸骨青色,腐爛食半,骨鎖在地,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
《中阿含•98經》:「如本見息道骸骨青色,爛腐餘半,骨璅在地,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
《中阿含•99經》:「若見彼姝息道,骸骨青色爛腐,餘半骨璅在地,於汝等意云何?」。[70]
在天台宗的《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與《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有數次提到「息道」,如: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卷1:「復次,一坐之中,身雖調和,而氣不調和。不調和相者,如上所說,或風、或喘、或復氣急,身中脹滿,當用前法隨而治之,每令息道綿綿,如有如無。」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2:「如上所說,或風喘、或氣急,身中脹滿,當用前法隨治之。每令息道綿綿,如有如無。」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4:「欲修安心,當教數息。所以者何?根本初禪多從數息中發,當知是人過去已曾數息修禪,今若從息道而入,與本相扶,禪則易發。」[71]
從前後文去理解「每令息道綿綿,如有如無」,似乎「息道」意指呼吸,如果將此一詞義用在上述的三部《中阿含經》上,卻與文義不合。
《中阿含•99經》的對應經典有漢譯的《苦陰經》、《增壹阿含•21.9經》與巴利《中部•13經》,在此首先與漢譯對應經文對比:
《苦陰經》:「『復次,當如見妹若死,一日至七日,若烏啄、若鵄啄,若狗食、若狐食,若火燒、若埋、若蟲。於意云何?前好容色寧敗壞不?』『唯然世尊!』『復次,如見妹死屍,若骨若青、若蟲若食、若骨白。於意云何?前好容色寧敗壞不?』」[72]
《增壹阿含•21.9經》:「世尊告曰:『是謂色為大患。復次,若見彼女人身,蟲鳥以食其半,腸胃肉血污穢不淨。云何,比丘!彼本有妙色,今致此變,於中起苦、樂想,此非大患乎?』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世尊告曰:『是謂色為大患。復次,若見彼女人身,血肉已盡,骸骨相連。云何,比丘!彼本有妙色,今致此變,於中起苦、樂想,此豈非大患乎?』」[73]
在英譯《中部尼柯耶》中,《中部•13經》此處的對應譯文為「skeleton骨骸」。[74]
各個譯本裡,這些「息道」、「死屍」、「身」、「skeleton」與巴利對應經文的sarira出現的位置相同,這個字在烏啄、狗食之前未出現,於次句才開始使用此字。因此,此處經文的「息道」應是指「骨骸」。
10.《法句經》:逝心、息心
《法句經》〈34 沙門品〉:「截流自恃,逝心却欲,仁不割欲,一意猶走。」[75]
在《佛般泥洹經》提到:「國有賢公,公名雨舍,雨舍公者,逝心種也。」[76]這一位阿闍世王跟前的「雨舍」,《長阿含•27經》譯為「雨舍婆羅門」,[77]由此可知,「逝心」是古譯,「婆羅門」是今譯。對應的巴利偈頌相當於巴利《法句經》383頌的前半段:
“Chinda sotaṃ parakkamma, kāme panuda brāhmaṇa”[78]
淨海法師譯為:「婆羅門!勇敢的截斷欲流,消除情欲」,[79]可以合理地推論漢譯《法句經》此處的「逝心」相當於巴利的「婆羅門brāhmaṇa」(此處為文法上的「呼格」)。
其他藏經版本《法句經》此處或作「近心」、「折心」,可以判為為訛寫,應以「逝心」為正。而《六度集經》:「昔者菩薩,時為逝心」、《佛說義足經》:「俱到逝心須加利講堂所」的「逝心」兩字,意指「婆羅門」。[80]
《法苑珠林》:「拘留國有逝心,名摩因提。」應是引自《佛說優填王經》:「拘深國有逝心,名摩因提。」《法句譬喻經》:「截流自持,折心却欲。」此處「折心」應是「逝心」,為「婆羅門」的較古譯語。[81]
漢譯經文另有「息心」一詞,一為「止息其心、寂靜其心」之意,一則為「沙門samaṇa」的譯詞。
《增壹阿含•49.8經》以「字源」的方式,解釋「沙門」的字義:
沙門名息心,諸惡永已盡,梵志名清淨,除去諸亂想。[82]
所以,《六度集經》下一引文的「息心」就是相當於「沙門」的古譯:
《六度集經》卷8:
人無尊卑令奉六齋,翫讀八戒帶之著身,日三諷誦,孝順父母,敬奉耆年,尊戴息心,令詣受經。鰥寡幼弱乞兒給救,疾病醫藥衣食相濟。[83]
《法句經》〈34 沙門品〉31, 32兩頌:
息心非剔,慢訑無戒,捨貪思道,乃應息心。
息心非剔,放逸無信,能滅眾苦,為上沙門。[84]
對應偈頌為《出曜經》〈33 沙門品〉13, 14兩頌:
比丘非剃,慢誕無戒,捨貪思道,乃應比丘。
息心非剃,放逸無信,能滅眾苦,為上沙門。[85]
從此處《出曜經》的第二頌,可以看出句首「息心」就是句末「沙門」,而《法句經》此處兩頌的「息心」也都意指「沙門」。
當然,經文中另有「息心」的用詞是意指「寂靜其心」,例如《中阿含•20經》:
波羅牢伽彌尼遙見世尊在林樹間,端正姝好,猶星中月,光曜暐曄,晃若金山,……諸根寂定,無有蔽礙,成就調御,息心靜默。[86]
《雜阿含•604經》:
此比丘知將死不久,勇猛精進,坐禪息心,終不能得道。[87]
三、藉助漢語文獻解讀詞義
漢譯佛典畢竟還是漢語文獻,有些詞義即使探求梵文或巴利經典也得不到合理的詮釋,反而應在魏晉文獻及對應的史書求得正解。所以,辛島靜志主張:「筆者認為在漢語裡可以解決的問題應該(在)漢語裡解決,不必提到梵文材料,把問題弄複雜。」[88]筆者認為,應該可以在此一主張的「梵文材料」加上「巴利文獻材料」。
以下筆者列舉經例,說明「藉助漢語文獻解讀詞義」的狀況。
11.《長阿含•7經》:採梠求財
《長阿含•7經》:
彼國有二人,一智一愚,自相謂言:「我是汝親,共汝出城,採侶求財。」[89]
《長阿含•7經》的對應經典有巴利《長部•23經》、《中阿含•71經》與《大正句王經》。《大正句王經》所舉的譬喻是「昔有二人薄有財賄,結伴經營」,[90]《中阿含•71經》所舉的譬喻是「猶如朋友二人捨家治生。」[91]都是兩人出門結伴作生意買賣。《長部•23經》所舉的譬喻是「兩人結伴去鄰近尋找值錢的東西」。[92]
《大正藏》經文「採侶求財」文句難以理解。宋版藏經作「採梠求財」,元、明版藏經作「採穭求財」。依據《一切經音義》「梠」字意為屋簷,也是與整段文意不符。[93]
《後漢書》(卷9)有與「采穭」相關的文句:「州郡各擁彊兵而委輸不至,群僚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飢死牆壁間,或為兵士所殺。」李賢註:「《埤倉》曰:『穭,自生也。』『稆』同『穭』。」
《一切經音義》卷66:「穭豆(上,力舉反。《埤蒼》云:『穭,苗自生也。』《文字典說》云:『不種自生也。』從禾、從魯聲也)。」[94]
綜合上述《後漢書》及《一切經音義》,「采稆」也寫作「采穭」,意即去摘採野生的稻子為食。《大正藏》「採侶求財」與宋版藏經「採梠求財」均應作「采稆求財」。而和元、明版藏「採穭求財」意思相同。
胡頌平提到胡適與周法高討論《長阿含•7經》「采稆求財」的意涵,胡適說:
鄙意以為六朝通行的「採穭」、「採稆」必已是引伸義居多了。《弊宿經》的譯者用用「採稆求財」四字,最可以表示當時通行的意義不是原始義,乃是引伸義。[95]
胡適認為「採稆的引申義」為「出門找機會發一點意外之財」,筆者雖然搜尋不到相關的漢語文獻支持此一解說,但是胡適此一詮釋與此處的巴利對應經文恰好相符。這樣的詞義詮釋可以從《妙法蓮華經文句》得到支持,如果「採稆」只是摘採野生稻、果充飢,就不用多次捨此取彼了。
答云:「如人採穭,初見麻取麻,次捨麻取麻皮,次捨麻皮取縷,次捨縷取布,次捨布取絹,次捨絹取銀,次捨銀取金。捨劣、取勝,云何不能捨?」[96]
12,《法句經》:精進難逾毀
《法句經》〈3 多聞品〉第1偈:
多聞能持固,奉法為垣牆,精進難踰毀,從是戒慧成。[97]
第三句「精進難踰毀」,宋、元、明版藏經作「精進難喻毀」。佛光版白話《法句經》解釋作:「在佛法方面精進不止,外在的詆毀就難以改變初衷。」[98]這樣的解釋並不恰當。
其實,此一偈頌的解釋可以參考《法句譬喻經》的〈3 多聞品〉:
問曰:「道人神變聖達乃爾,有琉璃城堅固難踰,志明意定,永無憂患,行何道德致此神妙?」道人答曰:「吾博學無厭,奉法不懈,精進持戒,慧不放逸,緣是得道自致泥洹。」[99]
「多聞能持固,奉法為垣墻」,即是《法句譬喻經》「吾博學無厭、奉法不懈」與「有琉璃城堅固難踰」,「精進難踰毀」可以類比作《法句譬喻經》「道人即化作琉璃小城以自圍遶,其人繞城數匝不能得入」,[100]這是「博學無厭,奉法不懈,精進持戒,慧不放逸」,以致如「琉璃小城」難踰難毀。所以,《大正藏》的「精進難踰毀」比宋、元、明版藏經「精進難喻毀」來得恰當。
在私人通訊中,紀贇教授指出此句的翻譯引用了漢語文獻的典故,如《尚書•費誓》「無敢寇攘逾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史記•魯周公世家》引作「無敢寇攘逾牆垣」,如此一來更加肯定此句是譯作「精進難踰毀」。
《法集要頌經•多聞品》有此頌的對應偈頌:
多聞能持固,奉法為垣墻,精進難毀譽,從是三學成。[101]
第三句「精進難毀譽」可能出自抄寫的差異,第四句「從是三學成」與「從是戒慧成」小有差異。
此一偈頌可能是犍陀羅《法句經》249偈(15〈Bahuśruta〉多聞品):
bahuṣuda dhama-dhara
sapraña budha-ṣavaka
śrudi-viñati akakṣu
ta bhaye’a tadhavidha
John Brough 在書中列巴利《長老偈》1030頌為對應偈頌:[102]
bahussutaṃ dhamma-dharaṃ
sappaññaṃ buddha-sāvakaṃ
dhamma-viññāṇaṃ ākaṅkhaṃ
taṃ bhajetha tathāvidhaṃ
(多聞者能持法,能親近佛聲聞弟子,期望能識法,被認為是佛弟子。)[103]
附帶一提,《大正藏》85冊,總經號2918,此為大英博物館藏燉煌寫本(S. 1638),經名擬作「《釋家觀化還愚經》」,其內容與《法句譬喻經•多聞品》此偈頌的詮釋相同,應該是自《法句譬喻經》抄出。[104]敦煌寫本原文即作《釋家勸化頑愚經》,《大正藏》的擬題有誤。經題《釋家觀化頑愚經》應作《釋迦勸化頑愚經》,這是抄寫訛誤。
13.《出曜經》:多喜忘誤
《出曜經》卷7〈5 放逸品〉:「無念及放逸者多喜忘誤,性意錯亂。」[105]
《大智度論》有類似的「喜忘」用語:
凡人為聞法故,從其聞說十二部經,以不能常得師故,皆當受持;以喜忘故,誦讀令利。[106]
曾良認為「喜」字意為「容易」,並舉出三個例子:[107]
《十誦律》卷37:「此衣舒在外邊喜失。佛言:『聽卷疊。』卷時喜舒。佛言:『以繩繫。』」[108]
《十誦律》卷37:「(佛語諸比丘:)『……聽汝等畜二種鉢:鐵鉢、瓦鉢。』瓦鉢喜破。佛言:『綴用。』」[109]
《十誦律》卷38:「時優波離問佛:『以何物作網?』佛言:『以毳,以蒭摩、劫貝、文闍草、麻、龍鬚皮等作。』作已喜爛壞。佛言:『應施雀目。』」[110]
依此解釋,《出曜經》的例句「無念及放逸者多喜忘誤」意為「不具念者及放逸者大多數容易忘失事物、容易誤記事物」。《大智度論》的例句「以喜忘故,誦讀令利」意為「因為容易忘失,所以應讀誦得順暢」。
14.《賢愚經》:宜稱使停
《賢愚經》:「鷹報王曰:『王為施主,等視一切,我雖小鳥,理無偏枉,若欲以肉貿此鴿者,宜稱使停。』」[111]
「停」字除了有停止的意涵之外,在古文還有「均衡、平均」的意思。《漢書》卷21:「權與物均而生衡。」[112]指的是「秤錘或天平上的法碼與待秤的物品等重(或力矩相等),就會產生平衡」。顏師古注:「孟康曰:『謂錘與物鈞,所秤適停,則衡平也。』」[113]《賢愚經》:「宜稱使停」,就是這樣的用詞,意為「斤兩相當、重量相同」。
方一新也提到《百喻經》的例子:[114]
爾時愚人聞此語已即自思念:「若不得留要當葬者,須更殺一子停擔兩頭乃可勝致。」於是便更殺其一子,而擔負之遠葬林野。[115]
引文「停擔兩頭」是指「擔子的兩頭重量均衡」,「乃可勝致」意為「才有辦法勝任將屍體擔到目的地」。
15.《雜譬喻經》:宜適
東漢支婁迦讖譯《雜譬喻經》列「人有十八難」:
有十八事,人於世間甚大難:一者值佛世難。二者正使值佛,成得為人難。……十三者正使至其所,得宜適難。十四者正使得宜適,受聽問訊說中正難。……是為十八事。[116]
同樣的經文也出現在失譯的《三慧經》:
有十八事,人於世間甚大難:一者值佛世難;二者正使值佛,成就得為人難。…十三者正使往至其所,得宜適難。十四者正使得宜適,聽問難。…是為十八事,人於世間大難。[117]
第十四難中之「宜適」,意義難曉。
周一良引《宋書,薛安都傳》「小子無宜適」、《後漢書,竇融傳》「遣從事問會見儀適」、《北史,魏收傳》「魏收恃才無宜適」,認為「宜適」與「儀適」互通,意為「禮節」,引申為「見面的禮物」。[118]
竺佛念翻譯的《出曜經》:「說法甘悅人,口出無量義,使我懷姙身,不羞此宜適。」[119]
宋、元、明版藏經「宜適」兩字的異寫正是「儀式」,周一良的主張與此暗合。
經文中「宜適」另有「安適、舒適」之意,例如,西晉白法祖翻譯的《佛般泥洹經》有經文:「飢飽寒熱,皆為苦極,身體難得宜適,皆不淨潔。」[120]此處「宜適」並不是指「禮物、禮節、儀式」,而是「安適、舒適」之意。至於附東晉錄、失譯人名的《般泥洹經》經文:「汝達於佛,而知宜適。」[121]此處「宜適」也是指「安適、舒適」,意為問候世尊身體是否安適。
16.《雜阿含•81經》:不足
漢土文獻中「不足」有兩種意涵,一是「不夠」,意指程度上或數量上的缺少,一是「不必、不需」。
前者如《論語》〈顏淵〉章「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道德經》77章「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孟子》〈梁惠王〉章「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
後者如《晉書》114卷「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資治通鑑》84卷「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此兩例「不足」都是指「不必」。
在漢譯佛典裡,如《雜阿含•81經》:「佛告離車摩訶男:『彼富蘭那為出意語,不足記也。』」[122]「不足記也」意為「不必記也」、「不需記也」。《增壹阿含•31.6經》:「今使五人皆持刀劍而隨汝後,其有獲汝者,當斷其命,不足稽遲。」[123]「不足稽遲」意為「不必停留延遲」。《增壹阿含•34.5經》:「時婦報曰:『但隨佛教,不足疑難。』」[124]此處「不足疑難」為「不必疑難」。《長阿含•2經》:「阿難答曰:『時既暑熱,彼村遠逈,世尊疲極,不足勞嬈。』」[125]此處「不足勞嬈」為「不必勞嬈」。
《雜阿含•1110經》:「不以畏故忍,亦非力不足。」這是講「不是力量不夠」。[126]《中阿含•8經》:「有時海水消盡,不足沒指。」[127]這是指海水消退,還不夠淹沒腳趾。
17.《雜阿含•91經》:不落度
《雜阿含•91經》:
何等為善知識具足?若有善男子不落度、不放逸、不虛妄、不凶險。如是知識能善安慰,未生憂苦能令不生,已生憂苦能令開覺,未生喜樂能令速生,已生喜樂護令不失,是名善男子善知識具足。[128]
此處「不落度」三字意思費解。《高僧傳》有「落度」一詞的用語可供參考。
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落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落度乎?」[129]
《高僧傳》記載佛圖澄因為佛塔一鈴獨鳴,向石宣解說此鈴講:「胡子落度」,事後,佛圖澄解說「胡子落度」不是應在石宣身上,而是說佛圖澄自己,他解釋說:「不用談享用『重茵美服』這樣的器用精美,出家人既不能居山修道,就是『落度』」。就前後文意看來,「落度」就是「落魄」、「不如意」。
周一良引《蜀志》10卷〈楊億傳〉:「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耶?」他認為此處「落度」應該是「落魄」之意,此一解釋可以遵從。[130]
18.《雜阿含•584經》:相屬
《雜阿含•584經》:「我無有族本,亦無轉生族,俱相屬永斷,解脫一切縛。……子俱是相屬。」[131]
此處「相屬」有「連續、相續」的意思。[132]如《史記》〈魏公子傳〉「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昭明文選》班固〈西都賦〉「都都相望,邑邑相屬」,《昭明文選》〈古詩十九首,東城高且長〉「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
在漢譯佛典中,例如:康僧會《六度集經》:「自斯之後日月無光,五星失度,妖怪相屬,枯旱穀貴。」[133]此處「相屬」也是「相續、連續發生」的意思。
在《雜阿含•584經》的對應巴利經文,與「相屬」相當的字是「santānakā子孫」,此字可以當作是巴利動詞「santāneti連續」的衍生字,「名詞santāna連續」加上「詞尾kā人」。[134]
在漢譯佛典「相屬」的意涵除了上述的「連續」之外,還有「勸人接續(跳舞或飲酒)」與「互相隸屬」兩種意思。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灌)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史記索隱》解釋為「相勸」。[135]可能類似近代的一種遊戲,一人跳舞(或飲酒)結束,可以指定同伴裡的一人接續跳舞,這一人跳完舞又可以指定下一個接替他跳舞的人。
「相屬」另有「勸留」之意,如《大樓炭經》:「男子便在前行,女人隨後行,至園觀入中,共相娛樂,二日、三日,若至七日,各自隨意罷去,不相屬也。」[136]
另外,如《雜阿含•226經》:「云何不計?謂不計我見色,不計眼我所,不計相屬。」[137]與《雜阿含•227經》:「彼比丘莫計眼我、我所,莫計眼相屬。」[138],此處「相屬」與「相在」意思相同,[139]也就是類似「色在我中、我在色中」的「互相隸屬」之意。[140]
19.《雜阿含•977經》:洛漠說、等分起
《雜阿含•977經》:「彼沙門婆羅門實爾洛漠說耳,不審不數,愚癡不善不辯。」[141]
「洛漠」或作「落漠」。《宋書•五行志》記載,有人自稱是「聖人所使」,下獄審問之後,「是東海縣呂暢,辭語落漠,髠,鞭三百,遣。」[142]
「落」字有一字義為「草木凋零」,《一切經音義》:「凋落(……下即各反,《說文》云:『草木凋襄也。』……)」[143]
《一切經音義》「漠」字的相關詮釋為:「《說文》……『漠』謂『北方幽冥沙漠也』,從水莫聲也。」[144]《說文》作「北方流沙也。」[145]
上引之《一切經音義》「草木凋襄」可能是「草木凋零」的訛寫。周一良引《宋書》「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為一旦落寞至此?」及「力作此答,無復條貫,貴布所懷,落漠不舉。」認為「落漠」是「疏略紕漏之意」。[146]
筆者認為,如果合併此條引文與《宋書》〈五行志〉「辭語落漠」看來,《雜阿含•977經》「落漠說」似乎是「言談誇大疏漏、沒有條理」的意思。
此一用語,到唐朝時仍然使用,例如義淨法師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譯文的小註「其放生器者,但為西國久行人皆共解,東夏先來落漠,故亦須委其儀。」[147]文意為「『放生器』這種濾出小蟲的器具,在印度施行已久,人盡皆知,來自東夏的唐人,剛到時較生疏易出紕漏,必須詳細了解此一器物與用法」。
又如《南海寄歸內法傳》:「向使早有人教行,法亦不殊王舍,斯乃先賢之落漠,豈是後進之蒙籠者哉?」[148]此處「蒙籠」意思與「朦朧」相當,應是「含糊」之意,而「落漠」則相當於「疏漏」。
《雜阿含•977經》後面經文有「等分起」的詞彙:「或從風起苦,眾生覺知,或從痰起,或從唌唾起,或等分起。」[149]
漢譯佛典「等分」有「平均分配」、「分成數量相同、大小均等的若干份數」的意思,例如:
《長阿含•2經》:「時諸國王即命香姓:『汝為我等分佛舍利,均作八分。』」[150]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爾時諸比丘與沙彌等分安居施物。」[151]
但是,《雜阿含•977經》此處經文顯然不是「平均分配」的意思。
《四諦論》:
復次病有二種:一身、二心。身病復有二種:一因界相違名緣內起,二因他逼觸名緣外起。是身病者。由名因處有差別故,品類多種。名差別者,謂漏、癩、癰、疽、氣、嗽、腫、癖、瘧、風狂等。因差別者,謂痰、風、膽及等分病。[152]
《佛本行集經》:
若體舊有諸餘雜病,或痿黃病,或風癲病,或痰癊病,或等分病,或餘諸病。[153]
《四諦論》列舉四種病因:「痰、風、膽及等分病」與《雜阿含•977經》相同,《佛本行集經》提到的病「或痿黃病,或風癲病,或痰癊病,或等分病」,如果「痿黃病」當作與「膽」相關的話,也是與《雜阿含•977經》相同。前者為南朝真諦所譯,後者為隋朝闍那崛多所譯,三人雖然年代不同,所譯的經論不同,但是面對相同的(或者至少是「類似的」)文句,都翻譯作「等分」。
從巴利對應經文《相應部•36.21經》來看,此處的對應用字為「visama」,「vi-離」「sama相等的」,意為「不平均的、不調和的」,如果依字面直翻的話,應該是「非等分的」、「不均等的」,似乎和譯詞「等分」正好相反。所以「等分」也許不是直接從「visama」翻譯得來的。
《大智度論》:「如意珠能除四百四病,根本四病:風、熱、冷、雜;般若波羅蜜亦能除八萬四千病,根本四病:貪、瞋、癡、等分。婬欲病分二萬一千,瞋恚病分二萬一千,愚癡病分二萬一千,等分病分二萬一千。以不淨觀除貪欲,以慈悲心除瞋恚,以觀因緣除愚癡,總上三藥或不淨、或慈悲、或觀因緣除等分病。」[154]
《大智度論》此處敘述,身體的根本四病「風、熱、冷、雜」與心志的根本四病「貪、瞋、癡、等分」對應,原先其他引文出現的「風、膽、痰、等分」相對於「風、熱、冷、雜」,可以理解《大智度論》的「雜」是前三者的混合、綜合而成的病,「等分」應該也可以如此解釋:「綜合各項的結果」。此處顯然不能以「visama不調和」來解釋「等分」,而是應如淨影《大智度論疏》的詮釋:「四病根本者,即風、熱、冷、雜,(雜)亦名等分。三病據偏發為言,等分據三種等起。」[155]也就是說,單獨一項病因(偏發)所造成的病,就稱此一病為「風」、「熱」或「冷」,如果有三種原因並起所造成的病,就稱為「等分」。例如《坐禪三昧經》:「若多婬欲人不淨法門治。若多瞋恚人慈心法門治。若多愚癡人思惟觀因緣法門治。若多思覺人念息法門治。若多等分人念佛法門治。諸如是等種種病,種種法門治。」[156]
筆者建議,不把「等分」當作「visama」的對譯,而認為「等分」在某些文脈之下,是指「各有前面數項的成分」或「前面數項的混合、綜合現象」。
20.《雜阿含•979經》:世尊疲極
《雜阿含•979經》:「莫逼世尊!世尊疲極。」[157]
《晉書》卷83〈顧和傳〉:「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此段史文描述顧和去見王導,王導略微倦累,在應對的時候疲睡。
《史記》卷83〈屈原列傳〉:「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天也。」
《昭明文選》卷47,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
「勞苦倦極」與「疾痛慘怛」對舉,可以知道「倦極」此詞的特性不是「非常疲倦」而是「疲倦」(「倦」、「極」都是「疲倦」)。從「人極馬倦」可知「極」也是「倦」。
所以,上引經文「世尊疲極」,應是「世尊疲倦」,而非「世尊非常疲倦」。
《雜阿含•711經》:「今來上山,四體疲極。」[158]
《雜阿含•1332經》:「止住一林中,入晝正受,身體疲極,夜則睡眠。」[159]
《雜阿含•571經》:「行路悶極。」[160]
《雜阿含•373經》:「飢餓困極。」[161]
以上經文的「極」字,都應作「倦」字解釋。
21.《雜阿含•1068經》:顧錄
《雜阿含•1068經》:
我是世尊姑子兄弟故,不修恭敬,無所顧錄,亦不畏懼。[162]
《大方便佛報恩經》:「汝師瞿曇,不知恩分,而不顧錄,遂前而去。」[163]
《法句譬喻經》:「其兒放縱無所顧錄,糶賣家物,快心恣意。」[164]
黃優良教授的論文指出「顧錄:顧睬。『錄』有『錄用、采納』義。」[165]依照「黃文」,「顧錄」如為「顧睬」,則是將「錄」等同為「睬」,「錄」字並無此義;如作「錄用、采納」義,置於原引文中,詞義並不相稱。
段玉裁注《說文》:「云『庸錄』者,猶『無慮』也。」「『慮』之假借也。」[166]朱熹《詩集傳》解釋〈魏風•碩鼠〉:「顧,念。」[167]字義也與「慮」字相近。
筆者認為「顧錄」的「錄」字,即是「念、慮」,「顧錄」可解釋為「顧慮」、「顧念」。
22.《雜阿含•1148經》:猶如鍮石銅
《雜阿含•1148經》中,波斯匿王見到外道出家形相莊嚴,因而起立、合掌問訊、自稱己名,他向佛陀解釋說:「世間若有阿羅漢者,斯等則是。」[168]
佛陀解釋應「觀其戒行,久而可知」,不可依外貌判定。最後以偈頌重述此意,第二首偈頌為:[169]
猶如鍮石銅,塗以真金色,
內懷鄙雜心,外現聖威儀,
遊行諸國土,欺誑於世人。」
《一切經音義》:「鍮石(上音「偷」,《埤倉》云:『鍮石似金,似而非金,西戎蕃國藥鍊銅所成。』)」[170]
所以「猶如鍮石銅」意為「猶如『鍮石』與『銅』」,而鍮石是金屬,不是石頭。《大唐西域記》:「伽藍東有鍮石釋迦佛立像,高百餘尺,分身別鑄,總合成立。」[171]既然是「分身別鑄」,可知是金屬。
周衛榮〈「鍮石」考述〉提到,支謙翻譯的《佛說阿難四事經》:「世人愚惑,心存顛倒,自欺自誤,猶以金價,買鍮銅也。」[172]也就是說,曹魏張揖的《埤倉》與孫吳支謙的譯經都已著錄「鍮石」這一用詞。周文也提到《舊唐書•輿服志》:「武德初,因隋舊制……五品以上……飾用金,……六、七品飾銀,八品、九品鍮石,……流外及庶人……飾用銅鐵。」所以「鍮石」的價值是在金銀之下、銅鐵之上。[173]
23.《雜阿含•1233經》:初不
漢土文獻中「初不」有兩義,一是「起初之時並不如此」;一是「完全不如此」,與時間前後無關。例如《魏書》:「(于簡)聲氣厲然,初不撓屈。」[174]《北齊書》:「(李稚廉)為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家人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輒擲之於地。」[175]此兩處「初不」都是「全不」之意。
《雜阿含•1233經》:
雖得財富,猶故受用麤衣、麤食、麤弊臥具、屋舍、車乘,初不嘗得上妙色、聲、香、味、觸,以自安身。[176]
《別譯雜阿含•150經》:
其第七者,常在道中,初不越逸,道雖微淺,明了知之,是名第七賢馬之相。[177]
此兩處經文「初不」意為「全不」、「完全不」。
《中阿含•33經》:
尊者阿難復作是說:「諸賢!我從如來受持八萬法聚,初無是心,我受此法,為教語他。諸賢!但欲自御自息,自般涅槃故。」[178]
《增壹阿含•32.10經》:
智者當惠施,初無變悔心,在三十三天,玉女而圍遶。[179]
此兩處經文「初無」的文意也應該是「全無」、「完全無」的意思。
24.《雜阿含•1342經》:親數
董志翹指出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刑餘之人,無所比數」,「比數」不是指「比擬、計數」,而是意為「親近」,此詞亦作「親數」。[180]
《雜阿含•1342經》:「與諸在家、出家周旋親數。」[181]
《佛本行集經》:
其後次至提婆達多童子前行,以貢高心我慢之心,不曾比數悉達太子,欲共太子捔競威力……。[182]
此兩處經文「比數」、「親數」都應該作「親近」解釋。
25.《中阿含•9經》:舉衣缽,《鸚鵡經》:藏舉
阿含經中有多處經文為「舉衣缽」,[183]例如:
《中阿含•9經》:
尊者舍梨子亦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國而行乞食,食訖,中後還,舉衣鉢,澡洗手足。[184]
《雜阿含•104經》:
爾時,尊者舍利弗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出城,還精舍,舉衣鉢已。[185]
《辭海》列舉十四個字義,似乎其中並無切合上述經文的義釋。[186]參照下列所引經文,「舉衣缽」相當於「舉藏應器」、「收舉衣鉢」、「攝舉衣鉢」,依「收舉」、「攝舉」、「舉藏」、「藏舉」的詞義,應該是「同義複合詞」,也就是說「舉」的字義與「收、攝、藏」相當,因此,「舉」字應該是意為「收藏」。[187]
《佛說義足經》:「子曹正各起座,到舍衛求食,食竟舉藏應器,還到祇樹入園,為佛作禮。」[188]
《中阿含•32經》:「於是,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鞞舍離城而行乞食,乞食已竟,收舉衣鉢,澡洗手足。」[189]
《雜阿含•272經》:「世尊責諸比丘故,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已,出,攝舉衣鉢,洗足,入安陀林,坐一樹下,獨靜思惟。」[190]
《增壹阿含•17.11經》:「是時,眾多比丘乞食已,還歸所在,攝舉衣鉢,往至世尊所。」[191]
《苦陰經》:「彼得錢財,便守護之、極藏舉之。」[192]
《鸚鵡經》:「當示我父遺財,汝本藏舉,我今不知處。」[193]
上引《鸚鵡經》的對應經文為《中阿含•170經》「若前世時是我父者,當示於我父本所舉金、銀、水精、珍寶藏處,謂我所不知。」[194],《中阿含•170經》的「舉」字,也應該是作「收藏」解。
《一切經音義》解釋「藏舉」為「藏弆」。[195]「弆」字是一個近代罕見的僻字,《一切經音義》解釋為「弆,藏也」。[196]
類似的用語如《雜寶藏經》卷2:「兄得此肉,藏弃不噉,自割脚肉,夫婦共食。」[197]董志翹解釋此處經文,認為「藏弃」應作「藏弆」,[198]意思即是「儲藏」。此兩字《大正藏》的校本「宋、元、明藏」作「藏舉」。[199]《法苑珠林》引此文作「兄得此肉,藏棄不敢食之,自割脚肉,夫婦共食。」[200]「藏棄」顯然不合理,因為後文提到「以先藏肉,還與弟食」[201],此肉是「先前所藏」,並未「拋棄」。此處《法苑珠林》引文的「藏棄」,「宋、元、明藏」也是作「藏舉」,「棄」字與「弆」字形體相近,有極大可能是因「弆」訛寫成「棄」。
有些經文除了將「藏弆」抄寫成「藏棄」之外,也抄寫成「藏去」。例如:
《生經》卷2:「於是比丘……明旦,著衣持鉢,入彼國邑,若於聚落,護諸根門,分衛始竟,飯食畢訖,藏去衣鉢,洗其手足。」[202]
總結此說,「藏弆」又作「藏舉」、「舉藏」、「藏去」、「藏棄」,[203]都應該是作「收藏」解釋。[204]
26.《中阿含•77經》:差降
《中阿含•77經》:「如是比丘必得差降安樂住止。」[205]
《大智度論》:「復次,佛田能獲無量果報,餘者雖言無量而有差降;以是故,佛田第一。」[206]
上述《大智度論》引文意為「其餘功德雖然也稱『無量』,但是隨其等級而有漸次差別。」有時「差降」近似於「高低差別」,如《鼻奈耶》:「時調達便起妬嫉意,向如來復作是念:『此沙門瞿曇生處種姓不能勝我,此亦釋種,我亦釋種,有何差降?』」[207]
但是,大部分使用「差降」的時候,是三個以上的項目,隨其等級的高低而有漸次的差別。如《宋史》卷173:「初,政和中,品官限田,一品百頃,以差降殺,至九品為十畝。」「殺」字為「減少」,「以『差降』殺」意為「依官品差別而遞減」。可以看出,雖然隨著品位的降低,田畝數量隨著減低,但是不需要遞減的數量完全一樣,只要是依次遞減即可。
「差降」並非僻字,不過,近代較少出現此一詞語。
27.《增壹阿含•24.8經》:為以世儉故作道耶
《增壹阿含•24.8經》:
世尊告曰:「汝等云何,為王種作道,為畏恐故作道,為以世儉故作道耶?」[208]
《說文解字》:「儉,約也。」[209]《廣雅•釋詁》:「儉,少也。」
「儉」字有兩種字義,一是儉省,為奢侈的相反詞。二是農作物歉收為「儉」,南北朝時,有「霜儉、水儉、旱儉」等詞語。例如《齊民要術》卷三:「且風、蟲、水、旱,饑饉薦臻,十年之內,儉居四五,安可不預備凶災也?」此段的文意為「而且風災、蝗害、水災、旱災、收成極壞等災害,重疊而至(薦臻),十年之內有四五年農作物歉收,怎麼能夠不儲備糧食來過荒年呢?」汪維輝於《《齊民要術》詞匯語法研究》書中解釋:「儉歲:荒年,歉收的年歲。(《齊民要術》):『橡子儉歲可食,以為飯;豐年放豬食之,可以致肥也。』」[210]
所以《增壹阿含•24.8經》「為以世儉故作道耶」意為「你們是因為饑荒才出家修道嗎?」同樣的經例還有《中阿含•66經》「是時,此波羅[木*奈]國災旱、早霜、蟲蝗,不熟,人民荒儉,乞求難得。」[211]
《增壹阿含•32.12經》:
應時之施有五事。云何為五?一者施遠來人,二者施遠去人,三者施病人,四者儉時施,五者若初得新菓蓏、若穀食,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是謂,比丘!應時之施,有此五事。[212]
對應的《增支部•5.36經》的用字正是「Dubbhikkha糧荒、饑荒」。
又如《廣弘明集》:「楊思達為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麥。」[213]此處正確的句讀應該是《廣弘明集》卷26:「楊思達為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麥。」「旱儉」指因乾旱而引起饑荒。
《別譯雜阿含•91經》「宜自籌量,不奢不儉,是名正理養命。」[214]此處經文為「儉約」,文意與「奢侈」相對。《別譯雜阿含•119經》「時世飢儉,乞食難得。」[215]此處經文為「饑荒」。
28.《增壹阿含•26.6經》:以口鳴如來足上
《增壹阿含•26.6經》:「阿難…復以口鳴如來足上。」[216]
《世說新語》有一則記載:
賈公閭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終無子。[217]
周一良指出,上引「充就乳母手中嗚之」南朝劉敬叔所著《異苑》作「就乳母懷中嗚撮」,「嗚之」、「嗚撮」都是親吻的意思,與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睒菩薩」章「嗚口吮足」意思相同。[218]
查閱《大藏經》,支謙譯的《梵摩渝經》「以口嗚佛足」也是親吻之意,可見此字用得甚早。[219]西晉竺法護譯的《生經》:「有人見與有嗚噈者,便縛送來。」[220]譯人不詳的《別譯雜阿含•3經》:「時,阿闍世抱取嗚唼,唾其口中。提婆達多貪利養故,即嚥其唾。」[221]同一事件,《大智度論》譯文為:「王子抱之,嗚唼與唾。」[222]「嗚撮」、「嗚唼」、「嗚噈」的「撮」、「唼」、「噈」可能是擬聲的字,用字雖然不同,三個詞應該都是親吻的意思。
玄應的《一切經音義》:「嗚噈(……『子六』、『子合』二反,《聲類》:『噈,亦嗚也』)。」[223]希麟的《續一切經音義》「或歍(下音烏,《切韻》云:『以口相就也。』《字書》云:『從欠,烏聲也。』《律文》從口作嗚,謂嗚呼哀歎聲,非歍唼義也。)。」[224]希麟認為「歍」是正字,「嗚」只適合用在「嗚呼」之類的哀嘆詞,不宜作為「口相就」的意思,玄應並沒有這樣的主張。周一良認為此兩字應該是「音義皆同」,參照前面所舉的例子,應該是兩字可以作為同義詞而相互通用。
由此可見,《增壹阿含•26.6經》「阿難……復以口鳴如來足上。」與《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時鄔陀夷……即摩觸彼身鳴唼其口。」[225]兩「鳴」字應該作「嗚」字,意為親吻。
四,一個詞義探討的案例:生藏、熟藏
《雜阿含•1165經》經文有「生藏、熟藏」:「腸、肚、生藏、熟藏、胞、淚……。」[226]明《徑山藏》此處作「生臟、熟臟」,此兩詞的確實意涵有待探討。
水野弘元《パ-リ語辭典》,āma-āsaya解釋為「生臟,胃」,pakka-āsaya解釋為「熟臟,S狀結腸與直腸」。[227]這樣的詮釋可能是來自Monier-Williams的《梵英字典》,但是將此兩字分別對應為「生臟、熟臟」應該是出自水野弘元的判斷。[228]筆者認為能否如此簡單地推定,仍有疑問。
就《雜阿含•1165經》經文而言,前文已經譯有「腸、肚」,如果「生藏、熟藏」又代表「胃、腸」,有重複列舉的嫌疑。同樣是「腸、胃、生熟藏」並列的譯文還有:
《方廣大莊嚴經》:「脾腎肝肺心,腸胃生熟藏。」[229]
《修行道地經》:「十四七日,生肝、肺、心及其脾、腎;十五七日,則生大腸;十六七日,即有小腸;十七七日,則有胃處;十八七日,生藏、熟藏起此二處。」[230]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肝、肺、脾、腎、大小腸、胃、膽、生熟藏、痰熱、心、肚。」[231]
以及清涼澄觀(西元737-838年)注疏的《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即〈涅槃十二聖行品〉云:從頭至足其中唯有髮(一)、毛(二)……脾(十一)、腎(十二)、心(十三)、肺(十四)、肝(十五)、膽(十六)、腸(十七)、胃(十八)、生藏(十九)、熟藏(二十)、大便(二十一)、小便(二十二)、涕(二十三)、唾(二十四)、目淚(二十五)……膀胱(三十五)、諸脈(三十六)。[232]
如果不談清涼澄觀的《疏》,中天竺沙門求那跋陀羅(《雜阿含經》)與地婆訶羅(《方廣大莊嚴經》)、敦煌竺法護(《修行道地經》),與留學那爛陀寺的玄奘(《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都是將「腸胃」與「生熟藏」並舉,觀想「身分」不需重複,因此這四項應該是不同的器官或留存於體內的食物。他們四人同時犯錯的可能性不高,因此,「生藏、熟藏」的本來字義應該考量、尊重漢譯對此詞的解釋,這也可能是不同傳承所保留的「異文」。
此詞最早出現在支謙翻譯的《撰集百緣經》:「汝等當知!我由先身惡口罵辱諸眾僧故,處此生、熟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難可叵當。」[233]
「生藏」也出現在《增壹阿含•36.3經》:「施人楊枝有五功德。云何為五?一者除風,二者除涎唾,三者生藏得消,四者口中不臭,五者眼得清淨。」[234]
義淨法師(西元635-713年)翻譯的《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有四戶蟲:一名師子,二名備力,三名急箭,四名蓮花,依生藏食生藏。有二戶蟲:一名安志,二名近志,依熟藏食熟藏。」[235]
《增壹阿含•12.1經》列舉28項「身分」,值得注意的是,經文將「生熟二藏」列在「屎、尿、淚、涕、唾」等體液、排泄物之間,而不是列在「腸、胃、心、肝、脾、腎」的器官分類裡。[236]
考量此三處譯詞,有可能譯者未將「生藏、熟藏」當作器官,而是指「留存體內的食物」。[237]
從跨文本對應經文的立場來看,《雜阿含•1165經》此段經文可以參照《相應部•35.127經》、《中部•10經》,此兩部經相當的句子都是「pihakaṃ papphāsaṃ antaṃ antaguṇaṃ udariyaṃ karīsaṃ」,[238]菩提比丘譯為「spleen脾,lungs肺,intestines腸,mesentery腸繫膜,contents of the stomach胃內(待消化的食)物,excrement糞便」。[239]《長部•22經》與此相當的經文,PED譯為「stomach胃,bowels肚,intestines腸」。[240]Maurice Walshe譯為「spleen脾,lungs肺,mesentery腸膜,bowels肚,stomach胃」。[241]可以看出,即使在巴利學界,這幾個字義也是很難得到共識。
那麼,《雜阿含•1165經》「生藏、熟藏」究竟是相當於巴利「udariya」、「antaguṇa」的對譯呢?還是相當於巴利「āma-āsaya」、「pakka-āsaya」的對譯呢?[242]
格拉斯(Andrew Glass)指出,巴利文獻中對於「身分」有三種不同版本。第一種版本列了31項,第二種版本列了19項,第三種版本列了21項。[243]如無著比丘也指出,《增壹阿含》列的「身分」只有24項,而相當的梵文版本則有36項。[244]梵文Śikṣāsamuccaya列有37項,而與此相當的漢譯《大乘集菩薩學論》則只列了31項。[245]依筆者的計算方式,如《增壹阿含•3.9經》有37項,但是其中脾(14, 25)、膀胱(19, 26)、尿(21, 27)重複,骨(8)與髑髏(36)應該也算是重複,還有百葉(22)、滄(23)、蕩(24)、[泳-永+羡](35)四個令人迷惑的譯詞,所以很難論斷《增壹阿含•3.9經》中的「身分」究竟列了幾項。在《中阿含•81經》與《中阿含•98經》都列了相同的33項,[246]不過薄膚(7)與皮(8)似乎只是一項,而非兩項,[247]唾(26)與涎(31)也是重複,這樣只有31項。《雜阿含•1165經》列了36項「身分」,但是不知沫(24)與癊(29)的確切意指,汁(33)是否應單獨列為一項,也頗值得懷疑。《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雖然明確地列了36項,但是「腦」重複出現在28與34兩項,而「骨」也重複出現在10與30兩項,似乎第30項的「骨」應該和第31項的「髓」併作「骨髓」一項。這也意味著原文上的編號可能是「清涼澄觀」之後的人所加,才會犯上重複的疏失。在《大乘集菩薩學論》列了31項「身分」,譯文中有「生藏、熟藏」而沒有「腸、胃」。《瑜伽師地論》則列有40項,「生藏、熟藏」位於「心、膽、肝、肺、大腸、小腸」與「肚、胃、脾、腎」之間,顯然是將「生藏、熟藏」視同身體器官之一。[248]
在眾多而混淆的「身分」敘述裡,必須理解《雜阿含•1165經》36項「身分」是譯自那一系統,才能指認「生藏、熟藏」對應的是那個印度語系的字詞。請參考<表一>。
附帶提及格拉斯文中的<表十>,梵文Śikṣāsamuccaya「身分」第15項kilomakaḥ與巴利「身分」第13項kilomakaṃ相當於「肋膜」,<表十>將之與漢譯「肺」對列,實際上漢譯「肺」應該列於巴利「身分」第15項papphāsaṃ。梵文Śikṣāsamuccaya「身分」第25項kheṭaḥ與巴利「身分」第28項kheḷo相當於「唾液」;梵文Śikṣāsamuccaya「身分」第26項siṅghāṇakam與巴利「身分」第29項siṅghāṇikā相當於「鼻涕」,<表十>的《雜阿含•1165經》列對了,但是,《中阿含•81經》兩者位置卻顛倒了,這項疏失可能是被《中阿含•81經》唾(26)與涎(31)的重複給困惑住了。[249]
格拉斯文中的<表十>顯示的字義,與菩提比丘的翻譯不同,實際上格拉斯也認為各種「身分」的確實涵義已經難以判定,而且有詞義往下一項「飄移」的現象。菩提比丘與格拉斯對幾個此處關注的字作不同的詮釋(梵文Śikṣāsamuccaya是antraguṇāmāśayaḥ,格拉斯解釋為antraguṇa與āmāśayaḥ兩字),筆者將相關項目列於<表二>,請參考<表二>。
<表一>梵、漢、巴利經論中的「身分」(SA 1165指《雜阿含•1165經》,Śik指梵文Śikṣāsamuccaya(筆者漢譯以格拉斯的英譯為依據)),[250]《大乘集學論》指《大乘集菩薩學論》(T1636),《華嚴疏鈔》指清涼澄觀的《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T1736),SN 35.127指《相應部•35.127經》(筆者漢譯以菩提比丘的英譯為依據),[251]EA 3.9指《增壹阿含•3.9經》,EA 12.1指《增壹阿含•12.1經》。
| SA 1165 | Śik | 《大乘集學論》 | 《華嚴疏鈔》 | SN 35.127 | EA 3.9 | EA 12.1 |
| 1髮 | 1髮 | 1髮 | 1髮 | 1髮 | 1髮 | 2髮 |
| 2毛 | 2毛 | 2毛 | 2毛 | 2毛 | 2毛 | 1毛 |
| 3爪 | 3爪 | 3爪 | 3爪 | 3爪 | 3爪 | 3爪 |
| 4齒 | 4齒 | 4齒 | 4齒 | 4齒 | 4齒 | 4齒 |
| 5塵垢 | 5塵 | | 6垢穢 | | | |
| 6網 | | 5不淨 | | | |
| 7皮 | 7皮 | 5皮膚 | 7皮 | 5皮 | 5皮 | 5皮 |
| 8肉 | 8肉 | 7肉 | 8肉 | 6肉 | 6肉 | 6肉 |
| 9白骨 | 9骨 | 10骨 | 10骨 (30重複) | 8骨 | 8骨 | 8骨 |
| 10筋 | 10筋 | 8筋 | 9筋 | 7筋 | 7筋 | 7筋 |
| 11脈 | 11脈 | 9脈 | 36諸脈 | | | 26脈 |
| 12心 | 13心 | 21心 | 13心 | 11心 | 13心 | 14心 |
| 13肝 | 21肝 | 23肝 | 15肝 | 12肝 | 11肝 | 15肝 |
| 31膽 | 24膽 | 16膽 | 20膽 | 10膽 | 28膽 |
| 14肺 | | 22肺 | 14肺 | 15肺 | 12肺 | |
| 15肋膜 | | | 13肋膜 | | |
| 15脾 | 14脾 | 25脾 | 11脾 | 14脾 | 14脾 (25重複) | 16脾 |
| 16腎 | 12腎 | 26腎 | 12腎 | 10腎 | 15腎 | 17腎 |
| 17腸 | 17大腸 | | 17腸 | 16腸 | 16大腸 | 12腸 |
| 16小腸 | | | | 17小腸 | |
| | 15膜 | 29膜 | 17腸繫膜 | 18白膜 | |
| 18肚 | 20胃 | | 18胃 | 18胃內食物 | | 13胃 |
| 19生藏 | 18生藏 | 27生臟 | 19生藏 | | | 20生藏 |
| 20熟藏 | 19熟藏 | 28熟臟 | 20熟藏 | | | 21熟藏 |
| 36胞 | | | 35膀胱(胞) | | 19膀胱 26泡(胞?) | |
| | 20咽喉 | | | | |
| 6.流涎 | 25涎 | 19唾 | 24唾 | 28涎 | 29唾 | 23唾 |
| 21淚 | 23淚 | 17淚 | 25目淚 | 26淚 | 28淚 | 22目淚 |
| 22汗 | 24汗 | 16汗 | | 24汗 | | |
| 23涕 | 26涕 | 18涕 | 23涕 | 29涕 | 30涕 | 24涕 |
| 24沫 | 28關節之間的潤滑液體 | | | 30關節之間的潤滑液體 | | |
| 25肪 | 27肪 | 12肪 | 27膏 | 27肪 | 33肪 | 27肪 |
| 26脂 | 30脂 | 13膏 | 26脂 | 25脂 | 34脂 | 11脂膏 |
| 27髓 | 29髓 | 11髓 | 31髓 | 9髓 | 9髓 | 9髓 |
| 28痰 | 32痰 | | | 21痰 | | |
| 29癊 | | | | | | |
| 30膿 | 33膿 | 31濃汁 | 32膿 | 22膿 | 31膿 | |
| 31血 | 34血 | 6血 | 33血 | 23血 | 32血 | 25血 |
| 32腦 | 35腦 | 14腦 | 28腦 (34重複) | | 37腦 | 10腦 |
| 36腦根 | | | | | |
| 33汁 | | | | | | |
| 34屎 | 22屎 | 29屎 | 21大便 | 19屎 | 20屎 | 18屎 |
| 35溺 | 37尿 | 30尿 | 22小便 | 31尿 | 21尿 (27重複) | 19尿 |
| | | | | 23滄(?) | |
| | | | | 24蕩(?) | |
| | | | | 22百葉(?) | |
| | | | | 35[泳-永+羡] | |
| | | | | 36髑髏 | |
<表二>菩提比丘與格拉斯的不同的詮釋(梵文Śikṣāsamuccaya是antraguṇāmāśayaḥ,格拉斯解釋為antraguṇa與āmāśayaḥ兩字)[252]
| 巴利經文 | 梵文Śikṣāsamuccaya | 格拉斯的英譯 | 菩提比丘的英譯 |
| antaṃ | | small intestines(小腸) | intestines(腸) |
| antaguṇaṃ | | large intestines(大腸) | mesentery(腸繫膜) |
| udariyaṃ | | contents of the stomach(胃內食物) | contents of the stomach(胃內食物) |
| antrāṇy | small intestines(小腸) | |
| antraguṇa | large intestines(大腸) | |
| āmāśayaḥ | Stomach(胃) | |
| pakvāśayaḥ | abdomen(肚) | |
在藏譯《俱舍論註》裡,三昧天(Samathadeva)引《阿含經》為《俱舍論》作註解,在相對於《俱舍論》第七章〈智品〉的註釋,本庄良文(Honjo Yoshifumi)翻譯的三昧天《阿含》引文中有類似的經文:「毛、爪、齒、埃、垢、皮膚、肉、骨、腱、脈、腎臟、心臟、脾臟、肺、生臟、熟臟、大腸、小腸、糞穢、肝臟、糞、淚、汗、洟、唾、肪、膏、髓、脂、膽汁、痰、膿、血、腦、膜、尿」,其中「生臟、熟臟」列於「大腸、小腸」之前,與<表一>所列七種文獻均不同。[253]
總結此段「生藏、熟藏」的探討如下:
1.「生藏」可能是譯自āma-āsaya,「熟藏」可能是譯自pakka-āsaya,但是在漢譯文獻裡前者不會是「胃」,後者不會是「S狀結腸與直腸」。
2.漢譯文獻裡,出現兩種不同的詮釋,一種是腹內食物尚未消化為「生藏」、腹內食物已消化快要成為糞便為「熟藏」,另一種是指身體器官,不能確知是指「腸上節、下節」還是指「胃、腸」
「生藏、熟藏」的漢譯可以顯示出,不管是「譯經事業」還在草創時期的支謙,或是已從印度回國的義淨,甚至是趙宋時代的法護,時間跨距長達八百年,[254]他們一致地將此對應字義翻譯成「生藏、熟藏」,或者是他們傳承的誦本、寫本此兩字與巴利傳承不同,或者是對同樣的兩字,他們傳承的字義與巴利註釋書傳統不同。[255]
3.漢譯文獻各個版本的「身分」,一部分有重複譯詞,代表譯者不是能夠完全正確掌握詞義。本庄良文論文中提到的藏譯三昧天《俱舍論伴隨》有相同的現象。[256]
4.格拉斯書中<表十>所列的漢譯「身分」,其對應位置有「肺、涎(唾)、涕」三處錯誤。[257]
5.從此一字義追尋的例子,可以說明:「未完全理解跨語言文本的全貌,而冒然從一、二對應經典去判斷字義,有犯錯的風險。」同時,除了倚賴現今梵、巴字典解釋字義之外,也不應忽略古漢譯對字義的詮釋。不管是認為古代譯師對原文、原典的理解一定高於現代的語言學家(philologist),或者認為現代學者在字義詮釋上一定勝過古代譯師,恐怕兩者都不是恰當的見解,而是必須針對各個字義,逐一剖析。
五、結語
《戴震集》〈《爾雅註疏箋補》序〉提到:
其究也,文字之鮮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鮮能通,妄謂通其心志,而曰傅合不謬,吾不敢知也。[258]
這句話是說「終究來說,如果有人自稱能通曉先聖的語言,卻讀不懂先聖的文字;讀不懂先聖的語言,卻自信能通曉先聖的心志,而能對先聖的談說、文字、思惟、著述的理解完全符合而無謬誤。這樣的主張,我不贊同。」
初期漢譯佛典的疑難詞釋義,可以藉由勘正經文、了解字義,正其標點句讀,提供更理想的知識背景來理解佛典的內容。我們可以將「佛典釋詞」歸納為兩類基本方法。第一類是純粹利用漢語訓詁方法,依據約略同期的漢語文獻來詮釋經義;第二類是利用跨語言文本的比較研究(cross-lingual comparative studies),將疑難詞的對應字句在其他文本(或其他語言文本)中定位,進而推測其可能的意義。
嚴格來說,第二類方法並不是「訓詁」或「詮釋」,只能算作一種「原典用字」的「構擬」。因為「對應經典」雖然與「漢譯經典」極為相似,卻無法保證「漢譯經典」的源頭文本與「對應經典」完全相同而一字不差;也就是說,雖然該字(或該句)的「對應經文」很有可能與「漢譯詞句」所對應的是同一字句,但是,也僅僅是止於「可能」而已。不同文本之間的「差異用字」也是常見的現象。這種差異,有時可以輕易判讀另一方為訛誤;有時,此類差異並沒有誰對誰錯的判定標準。
在處理「對應經典」的比較研究時,筆者常需自我警惕以避免不自覺地運用「單一文本」的假設,而忽略了「多元文本」的可能。蔡耀明教授在文章中引用Lamotte的意見來強調此點:
另一個必須納入考量的難題是說,就其印度的形貌而言,同樣的一部經典(會)隨著時間流逝繼而發生巨大的變化,並且還要做為翻譯成伊朗文、漢文、藏文等語文的依據對象,而這些譯本之間,也都存在顯著的歧異。造成這種現象的理由,在於這些譯本所依據的,就已經是彼此有所不同的傳本(recensions)。假如藉由將吾人手頭可差遣的材料屈從在一套文獻評定的作業程序(by submitting the material at our disposal to a process of textual criticism),而企圖把一部經典的原始文本(the Urtext of a sūtra)重建出來,這樣作下去,便註定是要走向失敗的結局。每一個傳本都有必要就其本身個別予以研究(Each recension requires its own study)。[259]
即使如此,筆者個人還是認為藉由這種「跨文本的比較研究」,在詮釋經義上總比「望文生義」或「詞義留白」來得合理一些,至少可以額外提供一種「詮釋」的選項。
六、謝詞
本文承蒙無著比丘於百忙之中協助詮釋部分巴利經文詞義,白瑞德教授提供對「生藏、熟藏」的補充意見,提示筆者未知或忽略的相關著作,這些建議或評論讓筆者得以修正部分謬誤,筆者在此致謝。本文初稿承蒙邱大剛詳細校讀,並提供不少補充資料,筆者也在此致謝。當然,本文如有任何謬誤,仍然是筆者應負的文責。
筆者也要向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全體工作人員致謝,沒有CBETA提供的全面而高效率的電子資料與工具,本文勢必無法完成必要的資料核對,也無法讓本文的部分構想成型。
本文執筆期間,筆者經常出入福嚴佛學院與法鼓佛教學院的圖書館,查閱書籍期刊。感謝院方及常住慈悲,讓筆者能就近參考這些重要佛教文獻。
開仁法師提示「9.息道」的可能詞義,鍾漢清提供胡適對「11.採侶求財」的解釋,陳炳坤與林淑敏提醒筆者對本文「19.洛漠說、等分起」與「4.補寫」兩個詞例進行詮釋,在此致謝。
最後,筆者感謝鍾漢清先生與新加坡佛教學院(BCS)紀贇博士的激勵,讓筆者注意到「佛典校勘學」的議題。
參考書目
一、英文或英文著作翻譯
Anālayo, Bhikkhu (2010), "The Influence of Commentarial Exegesi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Āgama Literature", in Translating Buddhist Chines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East Asia Intercultural Studies 3), pp. 1-20, K. Meisig (ed.), Wiesbaden: Harrassowitz.
Bodhi, Bhikkhu (2000),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Wisdom Publication, Boston, USA.
Brough, John (1962, 2001),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Delhi, India.
Lenz, Timothy, Glass, Andrew, Bhikshu Dharmamitra, (2003), A new Version of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and a Collection of Previous-Birth Stories,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USA and London, UK.
Malalasekera, G. P. (1937/1995 vol. 1, 1938/1998 vol. 2), Dictionary of Pāli Proper Names, Munshiram Manoharlal, Delhi, India.
Nattier, Jan (2008), 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Texts from the Eastern Han 東漢 and Three Kingdoms 三國 Periods,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X,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Tokyo, Japan.
Norman, K. R. (1995), The Group Discourses II, PTS, Oxford, UK.
Norman, K. R. (1997), 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The Bukkyō Dendō Kyōkai Letures 1994,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UK.
Nyanamoli, Bhikkhu and Bodhi, Bhikkhu (1995),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Wisdom Publication, Boston, USA. (2000 second print.)
Salomon, Richard (1999),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āndhāra: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USA and London, UK.
Waldschmidt, Ernst (1980), ‘Central Asian Sutra Fragments and their relation to Chinese Agama’, Die Sprache der Altesten Buddhistischen Überlieferung (edited by H. Bechert), pp. 136-174, Goettingen, Germany.
Zürcher, Erik (1977), ”Late Han Vernacular Elements in the Earliest Buddhist Translations” (〈最早的佛經譯文中的東漢口語成分〉),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中國語教師會會報》), vol. 12, 3rdissues, pp. 177-203.
Zürcher, Erik (1991), ‘A New Look at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exts’, in Koichi Shinohara and Gregory Schopen eds, From Benares to Beijing: Essays on Buddhism and Chinese Religion in Honour of Prof. Jan Yün-hua, Mosaic, Oakville, Ontario, pp. 277-300.
Zürcher, Erik (2007),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3rd edition, Leiden: E. J. Brill.
二、中文著作
印順法師(1971),《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正聞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印順法師(1983, 1994),《雜阿含經論會編》,正聞出版社,台北市,台灣,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初版,民國八十三年二月再版。
了參法師譯(1995),《南傳法句經》,向覺雜誌社,台北市,台灣。
淨海法師譯(1983),《真理的語言(法句經)》,Nārada Thera的英譯,正聞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淨海法師譯(2000),《真理的語言(法句經)》,德州佛教會玉佛寺,德州,美國。
無著比丘(2009),〈註釋書對阿含經文的影響〉,《正觀雜誌》第48期,頁1-48南投縣,正觀雜誌社,南投縣,台灣。
布歇(Boucher, Daniel) (1998),〈犍陀羅語與早期漢譯佛經的再思考---以《妙法蓮華經》為個案〉,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4,pp. 118. 中文為薩爾吉譯,朱慶之(編),(2009),《佛教漢語研究》,頁113-195,商務印書館,北京市,中國。
方一新(2004),〈作品斷代和語料鑒別〉,《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簡報》,2004.1,pp. 16-29,杭州市,中國。
杜曉莉(2006),〈「舉」字補說〉,《漢語史研究集刊》第9輯,頁362-369,巴蜀書社,成都市,中國。
段玉裁(注)(1985),《說文解字注》,東漢、許慎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5年重印「經韵樓藏版」,台北市,台灣。
李際寧(2002),《佛經版本》,《中國版本文化叢書》,江蘇古籍出版社,南京市,中國。
李際寧(2007),《佛教大藏經研究論稿》,《中國佛教學者文集》,朗宇法師主編,宗教文化出版社,北京市,中國。
李維琦(1994),《佛經釋詞》,岳麓書社,長沙市,中國。
李維琦(1999),《佛經續釋詞》,岳麓書社,長沙市,中國。
李維琦(2001),〈佛經釋詞再續(六則)〉,《古漢語研究》第2輯,頁89-92。
李維琦(2002),〈佛經釋詞再續〉,《漢語史學報》第2輯,頁154-158。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李維琦(2003),〈考釋佛經中疑難詞語例說〉,《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32卷第4期,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湖南,中國。
李維琦(2004),《佛經詞語匯釋》,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湖南,中國。
劉震(2011),〈用多種語文對勘來輔助漢文《大藏經》的新修工作〉,《第一屆「國際佛教大藏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81-293,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宜蘭縣,台灣。
林光明(2007),《光明論文選集》,嘉豐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林崇安(2003),〈「雜阿含」經文的釐正初探〉,《圓光佛學學報》第八期,頁1-27,圓光佛學院,中壢市,台灣。
梁曉虹(2001),〈論梵漢合璧造新詞〉。朱慶之(編),(2009),《佛教漢語研究》,頁284-306,商務印書館,北京市,中國。
盧巧琴(2011),《東漢魏晉南北朝譯經語料的鑒別》,浙江大學出版社,杭州市,中國。
顧滿林(2002),〈試論東漢佛經翻譯不同譯者對音譯或意譯的偏好〉,《漢語史研究集刊》第5輯,頁379-390,巴蜀書社,成都市,中國。
顧滿林(2005),〈東漢佛經音譯詞的同詞異形現象〉,《漢語史研究集刊》第8輯,頁325-337,巴蜀書社,成都市,中國。
顧滿林(2006),〈漢文佛典音譯詞的節譯形式與全譯形式〉,《漢語史研究集刊》第9輯,頁161-177,巴蜀書社,成都市,中國。
顧滿林(2007),〈漢文佛典中Kapila-vastu一詞的音譯形式考察〉,《漢語史研究集刊》第10輯,頁345-373,巴蜀書社,成都市,中國。
郭忠生(2010a),〈晝日住、入晝正受與宴默〉,《正觀雜誌》52期,頁5-112,南投縣,台灣。
郭忠生(2010b),〈關於《阿含經》與《尼柯耶》的對讀〉,《正觀雜誌》第55期,頁105-292,南投縣,台灣。
高明(2008),《中古史書詞匯論稿》,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市,中國。
高明道(1991),〈蟻垤經初探〉,《中華佛學學報》第四期,頁29-74,中華佛學研究所,台北市,台灣。
胡敕瑞(2004),〈《道行般若經》與其漢文異譯的互校〉,《漢語史學報》第4輯,頁127-146,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胡敕瑞(2005),〈中古漢語語料鑒別述要〉,《漢語史學報》第5輯,頁270-279,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胡適(1934),〈校勘學方法論—序陳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補釋例》〉,《胡適文集》第五集,頁108-119,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北京市,中國。
胡適(1946),〈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胡適文集》第十集,頁193-201,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北京市,中國。
黃征(2002),〈敦煌語言文字學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蘭州市,中國。
黃仁瑄(2011),《唐五代佛典音義研究》,中華書局,北京市,中國。
黃優良(2005),〈中古阿含部佛經詞語例釋〉,《泉州師範學院學報》,第23卷第5期,頁100-103,福建省,中國。
紀贇(2010),〈從口頭到書面—佛教文獻傳播方式的改變與大乘佛教的興起〉,《第一屆「國際佛教大藏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93,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宜蘭縣,台灣。
蔣禮鴻(1997),《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喬秀岩(2009),〈古籍整理的理論與實踐〉,《版本目錄學研究》第一輯,頁1-27,沈乃文編,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北京市,中國。
辛島靜志(1997, 1998),〈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裘雲青翻譯,《俗語言研究》1997年第4期、1998年第5期。朱慶之編(2009),《佛教漢語研究》,頁33-74,商務印書館,北京,中國。
辛島靜志(2003),〈《佛典漢語詞典》之編輯〉,《佛教圖書館館訊》,35/36期。
辛島靜志(2006),〈《撰集百緣經》的譯出年代考證—出本充代博士的研究簡介〉,《漢語史學報》第6輯,頁49-52,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辛島靜志(2007),〈早期漢譯佛教經典所依據的語言〉,徐文堪翻譯,《漢語史研究集刊》第10輯,頁293-305,巴蜀書社,成都市,中國。(Underlying Language of Early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n Christoph Anderl and Halvor Eifring eds., 《Studie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Christoph Harbsmeie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0th Birthday, Oslo, Hermes Academic Publishing, 2006, pp. 355-366》)
辛島靜志(2010),〈早期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以支婁迦讖及支謙的譯經對比為中心〉,《漢語史學報》第10輯,頁225-237,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辛島靜志(2011),〈利用「翻版」研究中古漢語演變—以《道行般若經》「異譯」與《九色鹿經》為例〉,《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總第18期,頁165-188,中正大學,嘉義縣,台灣。
徐時儀(梁曉虹、陳五雲)(2003),《佛經音義概論》,大千出版社,汐止鎮,台灣。
徐時儀(梁曉虹、陳五雲)(2005),《佛經音義與漢語詞彙研究》,商務印書局,北京,中國。
許理和Erik Zürcher著,蔣紹愚、吳娟譯(2009),〈最早的佛經譯文中的東漢口語成分〉,《語言學論叢》第14輯。(英文發表於《中國語教師會會報》(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第12卷第3期,1977年5月出版)。朱慶之(編)(2009),《佛教漢語研究》,頁75-112,商務印書館,北京,中國。
許理和著,顧滿林譯(2001),〈關於初期漢譯佛經的新思考〉(A New Look at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exts),《漢語史研究集刊》第4輯,頁288-312,巴蜀書社,成都市,中國。
朱慶之(1992),《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台北。
朱慶之(2000, 2001),〈梵漢《法華經》中的”偈”、”頌”和”偈頌”〉(一)、(二),《漢語史研究集刊》第3輯,頁176-192,《漢語史研究集刊》第4輯,頁328-344,巴蜀書社,成都市,中國。
朱慶之編(2009),《佛教漢語研究》,商務印書館,北京,中國。
周祖謨(1993),《方言校箋》,中華書局,北京市,中國。
周一良(1985, 2010),《魏晉南北朝史札記》,中華書局,北京市,中國。
周一良(1998),〈跋敦煌寫本《法句經》及《法句譬喻經》殘卷三種〉,《周一良全集》第三冊,頁280-285,遼寧教育出版社,瀋陽市,中國。
周衛榮(2000),〈「鍮石」考述〉,《文史》2000年第四輯,總第53輯,中華書局,北京市,中國。
張金霞(2005),〈顏師古的校勘學〉,《漢語史研究集刊》第8輯,頁374-414,巴蜀書社,成都市,中國。
張舜徽(2004),《張舜徽集》,(第一輯《中國文獻學》),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武昌市,中國。
張雲凱(2010),〈試論《雜阿含經》之「厭離」〉,《中華佛學研究》第11期,頁171-215,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新北市,台灣。
陳明(2003),〈新出安世高譯《七處三觀經》平行梵本殘卷跋〉,《西域研究》2003年第4期,頁59-65,科學出版社,北京市,中國。
陳明(2011),〈義淨譯經中的印度神名翻譯:文化認知與詞語選擇〉,《文史》2011年第三輯,頁127-145,中華書局,北京市,中國。
曾良(2011a),《敦煌佛經字詞與校勘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廈門市,中國。
曾良(2011b),〈佛經字詞考校五則〉,《文史》2011年第三輯,頁247-251,中華書局,北京市,中國。
蔡耀明(1998),〈判定《阿含經》部派歸屬牽涉的難題〉,法光雜誌,111期,台北市,台灣。
蔡耀明(2000),〈吉爾吉特(Gilgit)梵文佛典寫本的出土與佛教研究〉,《正觀雜誌》第13期,頁1-126,南投縣,台灣。
蔡耀明(2003),〈解讀有關《首楞嚴三昧經》的四篇前序後記—以《首楞嚴三昧經》相關文獻的探討為背景〉,《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8期,頁1-42,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台北市,台灣。
蘇錦坤(2009),〈再探漢巴文獻的〈比丘尼相應〉—馬德偉教授〈《別譯雜阿含經》的比丘尼相應〉一文的回應〉,《正觀雜誌》第51期,頁1-30,南投縣,台灣。
蘇錦坤(2010),〈從後說絕──單卷本《雜阿含經》是否將偈頌譯成長行〉,《正觀雜誌》第55期,頁5-104,南投縣,台灣。
蘇錦坤(2011),〈漢譯佛典校勘舉例——兼論印順導師與佛典校勘〉,《福嚴佛學研究》6期,頁23-72,新竹市,台灣。
萬金川(2009),〈梵本《維摩經》的發現與文本對勘研究的文化與思想轉向〉,《正觀雜誌》第51期,頁143-203,南投縣。此文也在《第四屆印度學研討會》發表,嘉義縣南華大學主辦,台灣。
溫宗堃(2006),〈巴利註釋書的古層〉,《福嚴佛學研究》第1期,頁1-31,福嚴佛學院,新竹市,台灣。
溫宗堃(2010),〈從巴利經文檢視對應的《雜阿含經》經文〉,《福嚴佛學研究》第5期,頁1-22,新竹市,台灣。
溫宗堃、蘇錦坤(2011),〈《雜阿含經》字句斠勘〉,《正觀雜誌》第57期,頁37-117,南投縣,台灣。
汪維輝(2007),《《齊民要術》詞匯語法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王邦維(2000),〈論阿富汗新發現的佉盧文佛教經卷〉,《中華佛學學報》第13期卷上,頁13-20,中華佛學研究所,台北縣,台灣。
王叔岷(2007),《斠讎學,校讎別錄》,(補訂本),中華書局,北京市,中國。
俞樾,(劉師培、楊樹達、馬敘倫、姚維銳)(2005),《古書疑義舉例五種》,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市,中國。
遇笑容(2006),〈梵漢對勘與中古譯經語法研究〉,《漢語史學報》第6輯,頁61-67,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遇笑容(2008),〈理論與事實:語言接觸視角下的中古譯經語法研究〉,《漢語史學報》第7輯,頁121-127,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三、日文或日文著作的翻譯
赤沼智善,Akanuma, Chizen, (1929, 1986 reprint at Taipei),《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The Compara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Agamas & Pali Nikayas 》,華宇出版社,台北縣,台灣。
丘山新、辛嶋靜志等譯,(2001),《現代語譯「阿含經典」--長阿含經》,平河出版社,東京都,日本。
四、網路資源
Online Sutta Correspondence Project. http://www.suttacentral.net/
台灣教育部《重訂標點符號手冊》修訂版(2008):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M0001/hau/c2.htm。
法雨道場(2007),《北傳法句經》,http://nt.med.ncku.edu.tw/biochem/lsn/newrain/canon/Khuddaka/fg.htm 嘉義縣,台灣。
法雨道場(2007),〈漢譯《法句經》與巴利《法句經》偈頌對照表〉,http://nt.med.ncku.edu.tw/biochem/lsn/newrain/canon/canon1.html 嘉義縣,台灣。
台灣教育部「異體字字典」(2012):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variants/
《法句經》、《出曜經》、《法集要頌經》偈頌對照表(2012):http://yifertwtw.blogspot.tw/
[1] 例如「不請」、「我許」、「交通」等等,這些語詞在漢語佛典語言學的專書與論文已經有充足的討論,本文不再重述這些詞例。相關的漢語佛典語言學書目可參考網址: http://yifertw.blogspot.com/2009/11/blog-post_29.html。
[2] 溫宗堃、蘇錦坤(2011)。蘇錦坤(2011)。
[3] 李維琦(1994, 1999, 2001, 2002, 2004)。
[4] 《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p. 311, a),《翻梵語》(CBETA, T54, no. 2130, p. 981a),《翻譯名義集》(CBETA, T54, no. 2131, p. 1056a)。
[5] 《雜阿含•267經》(CBETA, T02, no. 99, p. 69, c19-25)。
[6] 印順法師(1983),上册,頁71,4-5行,以及頁73,註4。
[7] 《雜阿含•267經》(CBETA, T02, no. 99, p. 69, c11-12),與(CBETA, T02, no. 99, p. 69, c15-17)。
[8] SN 22.100, S iii 151.
[9] 此處括號內的譯文為筆者所譯。相對於菩提比丘的英譯,他的譯文試圖將雙關的意思在單一的句子呈現出來。筆者認為《雜阿含•267經》「嗟蘭那鳥」應該是「嗟蘭那圖」的訛寫。《雜阿含•267經》「彼嗟蘭那鳥心種種故其色種種」(CBETA, T02, no. 99, p. 69, c21)此句應與「caraṇena cittena cittaññeva cittataraṃ 心的思維比『嗟蘭那』圖畫的顏色更多樣」相當,漢譯與巴利經文不同。「caraṇaṃ nāma citta稱為『嗟蘭那』的圖」菩提比丘譯為「that picture called faring on」,菩提比丘認為此句晦澀難解,但是仍然引用註釋書的解釋:「Spk-pṭ: because they take it and wander about with it. 因為帶著此圖畫去漫遊旅行(所以稱為「旅行的圖畫」)」,請參考Bodhi(2000), pp. 1088, note 206。筆者以為:「嗟蘭那圖」是一種「畫著講說內容的重要場景」的圖畫,旅行遊方的「說書人、政令宣導的官方使者」以此為輔助來講說故事。
[10] PED, p. 265, citta: painting. 請參考Bodhi(2000), pp. 958-959 以及 pp. 1088-1089, note 206 & 207。關於‘caraṇena cittena cittaññeva cittataraṃ’, PED, pp. 268, 解釋為‘S iii.151 sq. -- a punning passage, thus: by the procedure (caraṇa) of mind (in the past) the present mind (citta) is still more varied.’菩提比丘的英譯為‘yet the mind is even more diverse than that picture called Faring On’.兩者意思相當接近。陳明(2011),〈義淨譯經中的印度神名翻譯:文化認知與詞語選擇〉,頁133-134。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彩軍揵闥婆。」(CBETA, T16, no. 665, p. 446, a5)。梁朝,僧伽婆羅譯《孔雀王咒經》(CBETA, T19, no. 984, p. 451, c1)。
[11] 《出曜經》:「如是當觀身,如王雜色車,愚者所染著,善求遠離彼。」(CBETA, T04, no. 212, p. 738, b12-21)。《法集要頌經》:「如是當觀身,如王雜色車,愚者所染著,善求遠離彼。如是當觀身,如王雜色車,愚者所染著,智者遠離之。」(CBETA, T04, no. 213, p. 791, c1-4)。PED, p. 265, sucitta: gaily coloured or dressed. PED 此處為引用巴利《法句經》151頌。
[12] 《雜阿含•235經》(CBETA, T02, no. 99, p. 57, a17-19),巴利對應經典為 SN 35.150,此經在菩提比丘的英譯《相應部》經號為35.151,此經的相關語詮釋,請參考Bodhi(2000), pp. 1213-1214 以及 pp. 1420, note 148。
[13]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9, b6-7)。
[14] 《雜阿含•715經》(CBETA, T02, no. 99, p. 192, a28-29)。
[15] 《雜阿含•471經》(CBETA, T02, no. 99, p. 120, b21-22)。
[16] 《雜阿含•472經》(CBETA, T02, no. 99, p. 120, c14-17)。
[17] 《雜阿含•344經》:「云何於食如實知?謂四食。何等為四?一者粗摶食,二者細觸食,三者意思食,四者識食,是名為食。」(CBETA, T02, no. 99, p. 94, b29-c2)。
[18] 類似的經文,例如《中阿含•98經》:「樂食、苦食、不苦不樂食;樂無食、苦無食、不苦不樂無食。」(CBETA, T01, no. 26, p. 583, c28-29) 《中阿含•111經》:「樂食、苦食、不苦不樂食,樂無食、苦無食、不苦不樂無食。」(CBETA, T01, no. 26, p. 599, c17-18)。此則為源自無著比丘的教導。
[19] 《雜阿含•506經》(CBETA, T02, no. 99, p. 134, a7-9)。
[20] 《佛說義足經》(CBETA, T04, no. 198, p. 184, c25-27)。「濡軟」,《大正藏》校本的宋、元、明版藏經作「柔軟」。
[21] 《佛本行集經》(CBETA, T03, no. 190, p. 915, b11-14)。
[22] 《起世經》(CBETA, T01, no. 24, p. 342, b24-c1)。
[23] 《佛說立世阿毘曇論》(CBETA, T32, no. 1644, p. 225, a1-6)。
[24] 《大智度論》(CBETA, T32, no. 1644, p. 225, a1-6)。
[25] 《翻梵語》(CBETA, T54, no. 2130, p. 986, a22-23)。
[26] 《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p. 702, c20-21)。
[27] PED, pp. 404, ’kambala: woollen stuff, woollen blanket or garment’.
[28] Rhys Davids, T. W. and Stede, William, (1925), pp. 189, ‘paṇḍukambala: a light red blanket, orange-coloured cloth’.
[29] PED, pp. 610, ’vālakambala: a blanket made of horse-tails’.
[30] 《雜阿含•264經》(CBETA, T02, no. 99, p. 68, a25-26)。
[31] 《增壹阿含•50.4經》(CBETA, T02, no. 125, p. 807, b22-23)。
[32] Malalasekera, (1937/1995, 1938/1998), Sekka 條,書中對Paṇḍukambala-silāsana也單獨成立為一則詞條。
[33] 《雜阿含•612經》(CBETA, T02, no. 99, p. 171, c8-13)。
[34] 《中阿含•163經》(CBETA, T01, no. 26, p. 693, c7-23)。
[35] 《佛說身毛喜豎經》(CBETA, T17, no. 757, p. 600, a6-22)。
[36] 如果將對照《佛說身毛喜豎經》的巴利對應經典《中部•12經》,相當的英譯經文為:「except to eat, drink, consume food, taste, urinate, defecate, and rest in order to remove sleepiness and tiredness」(唯除食、飲、用食、味食、小便、大便和為了去除嗜睡與疲倦的休息),也可以判斷此一「定型句」提及「大小便事」,英譯經文根據 Nyanamoli and Bodhi(1995), p. 176-177。
[37] 《雜阿含•627經》(CBETA, T02, no. 99, p. 175, b4-7)。
[38] 黃優良(2005),頁103。
[39] 《雜阿含•542經》(CBETA, T02, no. 99, p. 140, c28-p. 141, a3)。
[40] SN 52.4, S v 298. Bodhi (2000), page 1754, line 20-21 譯為 "Friend Anuruddha, what are the things that a bhikkhu who is a trainee should enter and dwell in?" 此處筆者承無著比丘指導「vihātabbā」應作「viharati住於」的動名詞來理解。
[41] 「四雙八輩賢聖」,指「向須陀洹、得須陀洹,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阿羅漢、得阿羅漢,此是四雙八輩賢聖」,請參考《雜阿含•931經》(CBETA, T02, no. 99, p. 238, a6-8)。
[42] 《中阿含•66經》(CBETA, T01, no. 26, p. 509, b6-8)。《佛光阿含藏˙中阿含•66經》,頁470。
[43] 《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CBETA, T04, no. 199, p. 198, c2-4)。
[44] 《古來世時經》(CBETA, T01, no. 44, p. 829, b26-28)。
[45]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CBETA, T23, no. 1442, p. 899, a23-27)。
[46] 《中阿含•66經》(CBETA, T01, no. 26, p. 509, a10-11)。
[4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二),頁79,1行。
[48] 《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p. 472, c18)、(CBETA, T54, no. 2128, p. 736, a25)。
[49] 《中本起經》(CBETA, T04, no. 196, p. 158, c26-27)。
[50] 《中阿含•71經》(CBETA, T01, no. 26, p. 525, c19-21)。
[51] 《增壹阿含•46.7經》(CBETA, T02, no. 125, p. 777, b29)。
[52] 《佛本行集經》(CBETA, T03, no. 190, p. 685, a9-11)。
[53] 《中阿含•150經》(CBETA, T01, no. 26, p. 661, c9-12)。
[54] 筆者猜測,有可能「謶譏」為「謶个、謶介」的訛寫,「謶个、謶介」語音近似「cāga」,「个、介」字訛作「几」字,再訛為「幾」字。但是,這僅止於猜測,無可信的文證可支持此一假說。
[55] 郭忠生(2010b),頁134,8-9行。也可參考郭文的頁108-139,相關的「信、戒、聞、施、慧」的討論。
[56] 《中阿含•80經》(CBETA, T01, no. 26, p. 553, a20-22)。
[57] 《中阿含•98經》(CBETA, T01, no. 26, p. 582, b24-29)。
[58] 《中阿含•122經》(CBETA, T01, no. 26, p. 611, b3-6)。
[59] 《增壹阿含•4.2經》(CBETA, T02, no. 125, p. 557, b4-5)。
[60] 《中阿含•81經》(CBETA, T01, no. 26, p. 556, b11-14)。《中阿含•98經》(CBETA, T01, no. 26, p. 583, c1-3)。《中阿含•99經》(CBETA, T01, no. 26, p. 586, a1-3)。
[61] 《四書章句集註》第三冊,頁66。
[62] 《續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9, p. 976, c4-5)。
[63] 《一切經音義》(CBETA, T01, no. 26, p. 611, b3-6)。
[64] Anālayo(2011), pp. 82, line 8, 將「儀容庠序」翻譯作「with orderly manner and appearance」(整齊而有秩序的儀容),此處提到漢譯經文「儀容庠序」為對應的《中部•10經》與《長部•22經》所無。
[65] 《增壹阿含•38.9經》(CBETA, T02, no. 125, p. 724, a12-14)。「贍」為訛寫,正寫應為「瞻」。
[66] 《增壹阿含•39.8經》(CBETA, T02, no. 125, p. 732, b19-22)。
[67] 《菩薩從兜術天降神母胎說廣普經》(CBETA, T12, no. 384, p. 1051, b9-12)。
[68] 《佛本行集經》(CBETA, T03, no. 190, p. 822, b1-4)。漢譯四阿含經文,「審諦」有「明確」、「深思」、「真諦」等等意思,此處僅限於討論「視瞻審諦」的詞義。《一切經音義》載有「審諦」為「明確」的詞義:「髣髴(上芳同反。《漢書》云:『髣髴:相似,聞見不審諦也。』……)。」(CBETA, T54, no. 2128, p. 851, c23)
[69] 蔣禮鴻(1997),頁76-77。
[70] 《中阿含•81經》(CBETA, T01, no. 26, p. 556, b11-14)。《中阿含•98經》(CBETA, T01, no. 26, p. 583, c1-3)。《中阿含•99經》(CBETA, T01, no. 26, p. 586, a1-3)。
[71]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CBETA, T46, no. 1915, p. 466, b10-13);《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2(CBETA, T46, no. 1916, p. 490, b11-13);卷4 (CBETA, T46, no. 1916, p. 505, a11-14)。
[72] 《苦陰經》(CBETA, T01, no. 53, p. 847, c25-p. 848, a1)。
[73] 《增壹阿含•21.9經》(CBETA, T02, no. 125, p. 605, c15-23)。
[74] Nyanamoli, Bhikkhu and Bodhi, Bhikkhu, (1995),頁184,4行 。
[75]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2, b8-9)。《法句經》此一偈頌,《大正藏》「恃」字,《宋思溪藏》、《元普寧藏》與《明徑山藏》都作「忖」字;《大正藏》「割」字,此三部宋、元、明版藏經都作「害」字。
[76] 《佛般泥洹經》(CBETA, T01, no. 5, p. 160, b12-13)。
[77] 《長阿含•27經》(CBETA, T01, no. 1, p. 107, b6)。
[78] Dhammapada, Verse 383, pp. 108.
[79] 淨海法師(2000),頁107。
[80] 《增壹阿含•49.8經》(CBETA, T03, no. 152, p. 2, b8),(CBETA, T04, no. 198, p. 189, a17-18)。
[81] 《法苑珠林》(CBETA, T53, no. 2122, p. 444, a19-20)。《佛說優填王經》(CBETA, T12, no. 332, p. 70, c11-12)。《法句譬喻經》(CBETA, T04, no. 211, p. 604, b26-27)。
[82] (CBETA, T02, no. 125, p. 802, a29-b1)。
[83] 《六度集經》(CBETA, T03, no. 152, p. 49, a6-9)。
[84]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2, b16-18)。
[85]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766, a8-11)。《出曜經》與《法句經》的對應偈頌請參考: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2/11/t210-chapter-34-t04571c34.html。
[86] 《中阿含•20經》(CBETA, T01, no. 26, p. 445, b12-15)。
[87] 《雜阿含•604經》(CBETA, T02, no. 99, p. 164, a25-26)。
[88] 朱慶之編(2009),頁64,15-17行。此處引文為出自書中辛島靜志〈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一文。
[89] 本則詞義討論為鍾漢清所啟發。《長阿含•7經》(CBETA, T01, no. 1, p. 45, b3-5)。
[90] 《大正句王經》(CBETA, T01, no. 45, p. 834, c16-17)。
[91] 《中阿含•71經》(CBETA, T01, no. 26, p. 529, b19-20)。
[92] DN 23, D iii349. ‘āyāma, samma, yena so janapado tenupasaṅkamissāma, appeva nāmettha kiñci dhanaṃ adhigaccheyyāmā’。
[93] 《一切經音義》卷85:「寸梠(音呂。郭注《方言》云:『屋檐也』……)。」(CBETA, T54, no. 2128, p. 858, a17)。
[94] 《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p. 746, b4)。
[95] 胡頌平(1990),頁3083。
[96] 《妙法蓮華經文句》(CBETA, T34, no. 1718, p. 14, c2-5)。
[97]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0, a10-12)。
[98] 吳根友(1997),頁32。
[99] 《法句譬喻經》(CBETA, T04, no. 211, p. 578, c2-5)。此一段精文也見於大英博物館藏燉煌本(S. 1638),收錄於《大正藏》(CBETA, T85, no. 2918, p. 1462, c3- p. 1463, a5-10),經名擬作「《釋家觀化還愚經》」,其實是《法句譬喻經》殘本。
[100] 《法句譬喻經》(CBETA, T04, no. 211, p. 578, b18-20)。
[101] 《法句譬喻經》(CBETA, T04, no. 211, p. 578, c2-5)。此一段經文也見於大英博物館藏燉煌本(S. 1638),收錄於《大正藏》(CBETA, T85, no. 2918, p. 1462, c3- p. 1463, a5-10),經名擬作「《釋家觀化還愚經》」,其實是《法句譬喻經》殘本。
[102] Brough(1962, 2001: 158)。
[103] 此處漢譯為筆者所譯。
[104] 《法句譬喻經》(CBETA, T04, no. 211, p. 578, c2-5)。此一段經文也見於大英博物館藏燉煌本(S. 1638),收錄於《大正藏》(CBETA, T85, no. 2918, p. 1462, c3- p. 1463, a5-10),經名擬作「《釋家觀化還愚經》」,其實是《法句譬喻經》殘本。
[105]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647, c10)。
[106] 《大智度論》(CBETA, T25, no. 1509, p. 657, a11-13)。
[107] 曾良(2011a),頁2。
[108] 《十誦律》(CBETA, T23, no. 1435, p. 270, a18-20)。
[109] 《十誦律》(CBETA, T23, no. 1435, p. 269, b8-9)。
[110] 《十誦律》(CBETA, T23, no. 1435, p. 278, b19-22)。
[111] 《賢愚經》(CBETA, T04, no. 202, p. 352, a9-11)。
[112] 《漢書》,頁970。
[113] 《漢書》,頁971,注1。
[114] 方一新(2008),頁37,10-19行。
[115] 《百喻經》(CBETA, T04, no. 209, p. 543, c20-23)。
[116] 《雜譬喻經》(CBETA, T04, no. 204, p. 502, a8-21)。
[117] 《三慧經》(CBETA, T17, no. 768, p. 703, a24-b9)。
[118] 周一良(1985, 2010),頁206。
[119]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663, c25-26)。
[120] 《佛般泥洹經》(CBETA, T01, no. 5, p. 161, c11-13) 。
[121] 《般泥洹經》(CBETA, T01, no. 6, p. 185, a2)。
[122] 《雜阿含•81經》(CBETA, T02, no. 99, p. 20, c24-26)。
[123] 《增壹阿含•31.6經》(CBETA, T02, no. 125, p. 669, c11-13)
[124] 《增壹阿含•34.5經》(CBETA, T02, no. 125, p. 695, a24-25)。
[125] 《長阿含•2經》(CBETA, T01, no. 1, p. 20, c14-15)。
[126] 《雜阿含•1110經》(CBETA, T02, no. 99, p. 292, c4)。
[127] 《中阿含•8經》 (CBETA, T01, no. 26, p. 429, a9-10)。
[128] 《雜阿含•91經》(CBETA, T02, no. 99, p. 23, b7-11)。
[129] 《高僧傳》(CBETA, T50, no. 2059, p. 386, b9-12)。
[130] 周一良(1985, 2010),頁40。
[131] 《雜阿含•584經》(CBETA, T02, no. 99, p. 155, b12-19)。
[132] 周一良(1985, 2010),頁11:「《索隱》云:『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若今之舞訖相勸也。』」。
[133] 《六度集經》(CBETA, T03, no. 152, p. 25, c3-4)。
[134] SN 1.2.9, S i 8. 請參考水野弘元,《パ一リ語辭典》,頁289。
[135] 周一良(1985, 2010),頁11-12。
[136] 《大樓炭經》(CBETA, T01, no. 23, p. 280, b12-14)。
[137] 《雜阿含•226經》(CBETA, T02, no. 99, p. 55, c3-4)。
[138] 《雜阿含•226經》(CBETA, T02, no. 99, p. 55, c17-18)。
[139] 如《雜阿含•30經》「聖弟子於中見色是我、異我、相在不?」(CBETA, T02, no. 99, p. 6, b10-11)。
[140] 《雜阿含•109經》:「云何見我中色?謂見受是我,色在我中;又見想、行、識即是我,色在我中。云何見色中我?謂見受即是我,於色中住,入於色,周遍其四體;見想,行,識是我,於色中住,周遍其四體,是名色中我。」(CBETA, T02, no. 99, p. 34, b22-27)。
[141] 《雜阿含•977經》(CBETA, T02, no. 99, p. 252, c20-21)。日本正倉院聖語版《雜阿含經》此處「洛漠」兩字作「略演」。「約略演說」這個語意並不完全符合當時的情境,此處不予採用。
[142] 《宋書》卷34,〈五行志〉第二十四。
[143] 《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p. 339, c9-10)。
[144] 《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p. 874, b3-4)。
[145]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545,上欄。
[146] 周一良(1985, 2010),頁204。
[147]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CBETA, T24, no. 1451, p. 293, c4-5)。
[148] 《南海寄歸內法傳》(CBETA, T54, no. 2125, p. 218, c16-17)。
[149] 《雜阿含•977經》(CBETA, T02, no. 99, p. 252, c21-23)。
[150] 《長阿含•2經》(CBETA, T01, no. 1, p. 29, c20-21)。
[151]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CBETA, T22, no. 1421, p. 118, c26)。
[152] 《四諦論》(CBETA, T32, no. 1647, p. 382, c16-23)。
[153] 《佛本行集經》(CBETA, T03, no. 190, p. 685, b10-12)。
[154] 《大智度論》(CBETA, T25, no. 1509, p. 478, b14-20)。
[155] 淨影《大智度論疏》(CBETA, X46, no. 791, p. 877, c4-5 // Z 1:74, p. 221, a16-17 // R74, p. 441, a16-17)。引文中,小括號內第二個「雜」字,為筆者所加,原文僅有一個「雜」字。
[156] 《坐禪三昧經》(CBETA, T15, no. 614, p. 271, c2-5)。
[157] 《雜阿含•979經》(CBETA, T02, no. 99, p. 254, a15)。本則參考郭在貽(2005),頁22及頁105。
[158] 《雜阿含•711經》(CBETA, T02, no. 99, p. 191, a2-3)。
[159] 《雜阿含•1332經》(CBETA, T02, no. 99, p. 367, c19)。
[160] 《雜阿含•571經》(CBETA, T02, no. 99, p. 151, b25)。
[161] 《雜阿含•373經》(CBETA, T02, no. 99, p. 102, b24)。
[162] 《雜阿含•1068經》(CBETA, T02, no. 99, p. 277, b7-8)。
[163] 《大方便佛報恩經》(CBETA, T03, no. 156, p. 124, c7-8)。
[164] 《法句譬喻經》(CBETA, T04, no. 211, p. 596, b27-28)。
[165] 黃優良(2005),頁101。
[166]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703,上欄。
[167] 《詩集傳》〈魏風˙碩鼠〉,頁261。
[168] 《雜阿含•1148經》(CBETA, T02, no. 99, p. 305, c29-p. 306, a1)。
[169] 《雜阿含•1148經》(CBETA, T02, no. 99, p. 306, a13-18)。《相應部 3.2.1經》對應經文為:”Patirūpako mattikākuṇḍalova, Lohaḍḍhamāsova suvaṇṇachanno; Caranti loke parivārachannā, Anto asuddhā bahi sobhamānā.”(「就像陶製的假耳飾,就像外表塗金的銅幣;有些人偽裝而遊歷各處,內心不淨,外觀顯耀。」)。
[170] 《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p. 710, a24).
[171] 《大唐西域記》(CBETA, T51, no. 2087, p. 873, b15-17)。
[172] 《佛說阿難四事經》(CBETA, T14, no. 493, p. 757, a22-23)。
[173] 周衛榮(2000),頁79-89。但是漢地著作,已有將「鍮石銅」作為一物的書例,《梵網經菩薩戒略疏》卷5:「鍮:音偷,鍮石銅,似金。」(CBETA, X38, no. 695, p. 741, a8 // Z 1:60, p. 431, d14 // R60, p. 862, b14)。
[174] 《魏書》卷87,于什門。
[175] 《北齊書》卷43,李稚廉。
[176] 《雜阿含•1233經》(CBETA, T02, no. 99, p. 337, c15-17)。
[177] 《別譯雜阿含•150經》(CBETA, T02, no. 100, p. 430, b11-12),對應經文《雜阿含•925經》為「復次,良馬常隨正路,不隨非道,是名良馬第七之德。」(CBETA, T02, no. 99, p. 235, c3-4)。此處相對於「初不越逸」的經文為「不隨非道」,所以「初不越逸」的意思近於「全不越逸」,與「起初」之意無關。
[178] 《中阿含•33經》(CBETA, T01, no. 26, p. 473, b5-7)。
[179] 《增壹阿含•32.10經》(CBETA, T02, no. 125, p. 681, a16-17)。
[180] 董志翹(2009)。
[181] 《雜阿含•1342經》(CBETA, T02, no. 99, p. 370, a3)。
[182] 《佛本行集經》 (CBETA, T03, no. 190, p. 711, c21-23)。
[183] 本則的編寫受到董志翹(2007),《中古近代漢語探微》的啟發。
[184] 《中阿含•9經》(CBETA, T01, no. 26, p. 430, b18-20)。
[185] 《雜阿含•104經》(CBETA, T02, no. 99, p. 31, a7-8)。
[186] 《辭海》,頁2404-2405:「1. 兩手舉之,引申為舉手、舉足。2. 鳥飛。3. 稱舉。4. 薦舉。5. 攻拔。6. 祭。7. 記錄。8. 育子。9. 殺牲盛饌。10. 沒其財貨入官。11. 皆、凡。12. 廢舉。13. 重三兩曰舉。14. 姓。」
[187] 胡敕瑞(2002),頁22-24。董志翹(2007),頁157-159,稱為「同義複詞」。通常「同義複詞」可以交換字序,如「藏舉」、「舉藏」。
[188] 《佛說義足經》(CBETA, T04, no. 198, p. 178, b2-3)。
[189] 《中阿含•32經》(CBETA, T01, no. 26, p. 471, a2-4)。
[190] 《雜阿含•272經》(CBETA, T02, no. 99, p. 71, c15-18)。
[191] 《增壹阿含•17.11經》(CBETA, T02, no. 125, p. 586, c15-16)。
[192] 《苦陰經》(CBETA, T01, no. 53, p. 847, a14)。
[193] 《鸚鵡經》(CBETA, T01, no. 79, p. 889, a16)。
[194] 《中阿含•170經》(CBETA, T01, no. 26, p. 704, b29-c2)。
[195] 《一切經音義》:「藏舉(……有經本或作『弆』。……)。」(CBETA, T54, no. 2128, p. 372, a13)。
[196] 《一切經音義》卷57:「密弆(『姜語反』。弆,藏也)。」(CBETA, T54, no. 2128, p. 689, b20)。
[197] 《雜寶藏經》(CBETA, T04, no. 203, p. 458, c10-11)。
[198] 董志翹(2007),頁69-70。
[199] 依據《大正藏》,《大正藏》所稱的「宋版大藏經」意指「南宋思溪藏」,「元版大藏經」意指「元大普寧寺藏」,「明版大藏經」意指「明方冊藏」。
[200] 《法苑珠林》(CBETA, T53, no. 2122, p. 776, c1-2)。
[201] 《雜寶藏經》(CBETA, T04, no. 203, p. 458, c11-12)與《法苑珠林》(CBETA, T53, no. 2122, p. 776, c3)。
[202] 《生經》(CBETA, T03, no. 154, p. 82, b2-6)。
[203] 作「藏舉」,如《增壹阿含•18.2經》「所謂得財物恒藏舉之。」(CBETA, T02, no. 125, p. 587, b18-19),《大寶積經》:「是我父物。將置身邊或時藏舉。」(CBETA, T11, no. 310, p. 7, a17-18)。作「舉藏」,如《佛說義足經》:「子曹正各起座,到舍衛求食,食竟舉藏應器,還到祇樹入園,為佛作禮。」(CBETA, T04, no. 198, p. 178, b2-3),《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乃至施衣時應畜者。謂舉藏也。」(CBETA, T23, no. 1442, p. 754, c22-23)。作「藏去」,如《寂志果經》:「藏去珍寶,求索其處。」(CBETA, T01, no. 22, p. 273, b5),《佛說罵意經》卷1:「譬如有人直取一物觀視已,便藏去之。」(CBETA, T17, no. 732, p. 532, a22-23)。作「藏棄」,如《法苑珠林》卷37:「若塔僧物,賊來急時,不得藏棄。」(CBETA, T53, no. 2122, p. 580, b22-23)。
[204] 杜曉莉(2006),頁365,21-23行:「但是,我們發現,『舉』的『藏』義和它的『收攏』、『放置』義有明顯的源流關係,不必解釋為『弆』的借字。」 筆者不贊同此一意見,實際上從「異文」可以觀察到「舉弆」被訛寫為「舉去」。「舉」字不是「弆」的借字,只是「弆」字漸漸成為僻字而廢棄不用,轉寫時,多寫作「舉」字。
[205] 《中阿含•77經》(CBETA, T01, no. 26, p. 545, c4)。
[206] 《大智度論》(CBETA, T25, no. 1509, p. 282, b12-14)。
[207] 《鼻奈耶》(CBETA, T24, no. 1464, p. 859, b13-16)。
[208] 《增壹阿含•24.8經》(CBETA, T02, no. 125, p. 626, b18-20)。宋、元、、明版藏經「儉」字作「險」字。古籍於「儉」、「險」兩字常互通,如《論語》:「小人行險以僥倖」,或作「小人行儉以僥倖」。
[209] 《說文解字注》,頁376,上欄,段注:「古假『險』為『儉』,《易》『儉德辟難』,或作『險』」。
[210] 汪維輝(2007),頁226。
[211] 《中阿含•66經》(CBETA, T01, no. 26, p. 508, c24-26)。
[212] 《增壹阿含•32.12經》(CBETA, T02, no. 125, p. 681, b17-c3)。
[213] 《廣弘明集》(CBETA, T52, no. 2103, p. 294, b7-8)。亦可見《顏氏家訓˙歸心》:「楊思達為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麥。」
[214] 《別譯雜阿含•91經》(CBETA, T02, no. 100, p. 405, a14-15)。
[215] 《別譯雜阿含•119經》(CBETA, T02, no. 100, p. 417, c10)。
[216] 《增壹阿含•26.6經》(CBETA, T02, no. 125, p. 637, a20-21)。
[217] 《世說新語》,第三十五篇〈惑溺篇〉,第三則。
[218] 《六度集經》(CBETA, T03, no. 152, p. 24, b14)。周一良(1985, 2010),頁49,〈《晉書》改易史料文字〉則。
[219] 《梵摩渝經》(CBETA, T01, no. 76, p. 885, c10)。
[220] 《生經》(CBETA, T03, no. 154, p. 78, c22) 。
[221] 《別譯雜阿含•3經》(CBETA, T02, no. 100, p. 374, b17-18) 。
[222] 《大智度論》(CBETA, T25, no. 1509, p. 164, c22-23) 。
[223] 《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p. 674, c23) 。
[224] 《續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9, p. 973, c7) 。
[225]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CBETA, T23, no. 1443, p. 994, b18-19) 。
[226] 《雜阿含•1165經》(CBETA, T02, no. 99, p. 311, a29-b1)。
[227] 水野弘元(1968),頁51,左欄與頁152,左欄。
[228] Monier-Williams (1899), pp. 146.
[229] 《方廣大莊嚴經》(CBETA, T03, no. 187, p. 574, a13)。
[230] 《修行道地經》(CBETA, T15, no. 606, p. 187, a20-23)。
[231]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CBETA, T27, no. 1545, p. 208, a23)。
[232]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343, b18-23)。
[233] 《撰集百緣經》(CBETA, T04, no. 200, p. 250, c8-11)。這是印度古說,稱「胞胎」位於「生藏」、「熟藏」之間,此一見解不符現代醫學知識。《七處三觀18經》:「髮、毛、爪、齒、血脈、肌肉、筋骨、脾、腎、大腸、小腸、大腹、小腹、大便、小便、淚、汗、涕、唾、肝、肺、心、膽、血、肥膏、髓、風、熱、頂[寧*頁]」(CBETA, T02, no. 150A, p. 878, c16-18),如《七處三觀18經》為安世高所譯,而且「大腹、小腹」意為「生藏、熟藏」,則此一詞彙可以更往前追溯到安世高時期。
[234] 《增壹阿含•36.3經》(CBETA, T02, no. 125, p. 703, a11-14),對應經典是《增支部•5.208經》,可惜的是《增壹阿含•36.3經》解說《增壹阿含•36.3經》使用楊枝的功德,而《增支部•5.208經》則是解說不使用楊枝的缺陷,沒有和「生藏」對應的字。
[235]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CBETA, T24, no. 1451, p. 257, a2-5)。可參考《大寶積經》卷55:「有四戶蟲:一名意樂,二名師子力,三名兔腹,四名耽欲,依止生藏而食生藏。有二戶蟲:一名勇猛,二名勇猛主,依止熟藏食於熟藏。」(CBETA, T11, no. 310, p. 325, b13-16)。
[236] 《增壹阿含•12.1經》:「復觀此身有毛、髮、爪、齒、皮、肉、筋、骨、髓、腦、脂、膏、腸、胃、心、肝、脾、腎之屬,皆悉觀知。屎、尿、生熟二藏、目淚、唾、涕、血、脈、肪、膽,皆當觀知,無可貪者。」(CBETA, T02, no. 125, p. 568, a19-22)。
[237] 《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3:「人腸上節,食未變是生藏。下節變為糞穢,名熟藏。」(CBETA, T40, no. 1805, p. 389, c26-27),意指「位處於腸上節的食物」為「生藏」,「位處於腸下節的食物」為「熟藏」。此為漢地注疏,不是譯文,僅能作為原文字義的參考。
[238] SN 35.127, S iv 111; MN 10, M i 57.
[239] Bodhi (2000), pp. 1198, line 9-10. 此一譯文與 Honrer (1976) 相同,請參考 Horner (1976), pp. 74, line 1-2. 中文為筆者所譯。
[240] PED, pp. 1198, line 9-10. 此一譯文與 Honrer (1976) 相同,請參考 Horner (1976), pp. 74, line 1-2. 中文為筆者所譯。
[241] Walshe (1987, 1995), pp. 337, line 21-22. 中文為筆者所譯。
[242] 對於今本漢譯《雜阿含經》(T99)依據的源頭文本,雖然學者對其部派歸屬與源頭語言有些推論,但是都還不足以成為定論。此處為行文方便,雖然列舉的是巴利拼寫,意指與此字相當的印度語系文字,可能是梵語、俗語、犍陀羅語,也有可能是與上列不同的另一種語言。
[243] Glass (2007), pp. 52-54. 特別是53頁的表10最值得參考,但是表10也有一些小瑕疵,請參考下文敘述。
[244] Anlayo (2003), pp. 146, note 116.
[245] Glass (2007), pp. 52-54, table 10. Bendall (1902), pp. 209, line 8-11.《大乘集菩薩學論》:「髮、毛、爪、齒、皮膚、血、肉、筋、脈、骨、髓、肪、膏、腦、膜、汗、淚、涕、唾、咽喉、心、肺、肝、膽、脾、腎、生臟、熟臟、屎、尿、濃汁。」(CBETA, T32, no. 1636, p. 117, b20-22)。
[246] 《中阿含•81經•念身經》與《中阿含•98經˙念處經》:「1髮、2毛、3爪、4齒、5塵、6網、7薄膚、8皮、9肉、10筋、11骨、12心、13腎、14肝、15肺、16大腸、17小腸、18脾、19胃、20摶糞、21腦及22腦根、23淚、24汗、25涕、26唾、27膿、28血、29肪、30髓、31涎、32膽、33小便。」(CBETA, T01, no. 26, p. 556, a14-16)(CBETA, T01, no. 26, p. 583, b6-9)。
[247] 《中阿含•81經•念身經》與《中阿含•98經•念處經》:「1髮、2毛、3爪、4齒、5塵、6網、7薄膚、8皮、9肉、10筋、11骨、12心、13腎、14肝、15肺、16大腸、17小腸、18脾、19胃、20摶糞、21腦及22腦根、23淚、24汗、25涕、26唾、27膿、28血、29肪、30髓、31涎、32膽、33小便。」(CBETA, T01, no. 26, p. 556, a14-16)(CBETA, T01, no. 26, p. 583, b6-9)。
[248] 《瑜伽師地論》卷26:「1髮、2毛、3爪、4齒、5塵、6垢、7皮、8肉、9骸、10骨、11筋、12脈、13心、14膽、15肝、16肺、17大腸、18小腸、19生藏、20熟藏、21肚、22胃、23髀(脾)、24腎、25膿、26血、27熱、28痰、29肪、30膏、31肥、32髓、33腦、34膜、35洟、36唾、37淚、38汗、39屎、40尿。」(CBETA, T30, no. 1579, p. 428, c24-27)。
[249] 這一點得自白瑞德(Rod Bucknell) 私人通訊裡給筆者的提示。
[250] Glass (2007), pp. 54 line 27-34:”Head hair, body hair, nails, teeth, dust, dirt, skin, flesh, bone, sinew, blood vessels, kidneys, heart, spleen, pleura, small intestine, large intestine, stomach, abdomen, bladder, liver, fecal matter, tear fluid, sweat, saliva, mucus, grease, joint fluid, bone marrow, fat, bile, phlegm, pus, blood, head, brain, and urine.”
[251] Bodhi (2000), pp. 1198 line 7-11: ”head-hairs, body-hairs, nails, teeth, skin, flesh, sinews, bones, bone-marrow, kidneys, heart, liver, pleura, spleen, lungs, intestines, mesentery, contents of stomach, excrement, bile, phlegm, pus, blood, sweat, fat, tears, grease, saliva, snot, fluid of joint, urine.” Glass (2007)有與此相當的譯文,請參考 pp. 54 line 1-7。
[252] 格拉斯文中的<表十>,將āmāśayaḥ對應「生藏」,將pakvāśayaḥ對應「熟藏」。
[253] 本庄良文(1998),頁92,24-29行。本庄良文在頁93,9-10行提及「讀解困難」。
[254] 筆者略估支謙的譯經年代為西元220年,距法護翻譯的《大乘集菩薩學論》(《閱藏知津》「《大乘集菩薩學論》(二十五卷今作十一卷),法稱菩薩造,宋中印土沙門法護等譯」(CBETA, J32, no. B271, p. 152, c12-13)),約800年,誤差不會超過五十年。
[255] 《七處三觀•18經》:「觀是身有髮、毛、爪、齒、血脈、肌肉、筋、骨、脾、腎、大腸、小腸、大腹、小腹、大便、小便、淚、汗、涕、唾、肝、肺、心、膽、血、肥、膏、髓、風、熱、頂[寧*頁]。」(CBETA, T02, no. 150A, p. 878, c16-18)有31項「身分」,筆者推估「大腹、小腹」可能是「生藏、熟藏」的對譯。
[256] 本庄良文(1998),頁92,24-29行。
[257] Glass (2007), pp. 53, table 10.
[258] 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著(2010),《戴震全集》第六冊,頁274-275,〈《爾雅註疏箋補》序〉。
[259] 譯文引自蔡耀明(2003),頁16。